版权所有©2013作者(s)。由韧性联盟授权在此发布。
去pdf本文的版本
去pdf本文的版本
以下是引用这篇文章的既定格式:
Muttarak, R.和W. Pothisiri. 2013。教育在防灾准备中的作用:2012年印度洋地震在泰国安达曼海岸的案例研究。生态和社会 18(4): 51。
http://dx.doi.org/10.5751/ES-06101-180451
研究,一部分的特别功能教育与自然灾害脆弱性差异
Muttarak, R.和W. Pothisiri. 2013。教育在防灾准备中的作用:2012年印度洋地震在泰国安达曼海岸的案例研究。生态和社会 18(4): 51。
http://dx.doi.org/10.5751/ES-06101-180451
教育在防灾准备中的作用:以2012年印度洋地震泰国安达曼海岸为例
1维特根斯坦人口与全球人力资本中心(IIASA, VID/ÖAW和WU),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2朱拉隆功大学人口研究学院
摘要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调查了在泰国攀牙省安达曼海岸的居民如何做好地震和海啸的准备。有人假设,正规教育可以促进防灾准备,因为教育提高了个人的认知和学习技能,以及获取信息的机会。对2012年4月11日印度洋地震后收到海啸警报的地区的557户家庭进行了调查。采访是在多次余震期间进行的,这使该地区的居民处于高度警惕状态。受访者被问及在4月11日地震后采取了哪些应急准备措施。利用部分比例优势模型,本文调查了个人灾害准备的决定因素,衡量为采取的准备行动的数量。在控制了村庄效应后,我们发现,在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衡量的正规教育与采取防范措施呈正相关。对于没有灾害经历的调查群体,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与防灾准备呈正相关。研究结果还表明,与灾害相关的培训对教育程度高的人最有效。此外,生活在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妇女比例较高的社区,会增加备灾的可能性。 In conclusion, we found that formal education can increase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duce vulnerability to natural hazards.
关键词:防灾;地震;教育;部分比例比值模型;泰国;海啸
介绍
虽然仍然无法预测地震将在何时何地发生,但可以通过采取各种个人安全措施来减少地震灾害的影响(Turner et al. 1986, Lehman and Taylor 1987, Ramirez and Peek-Asa 2005)。同样,海啸(由海底地震引起的巨大海浪)带来的灾难可以通过有效的预警系统减轻或避免。事实上,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的灾难性损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预警系统的缺乏、知识的缺乏和风险人群的准备不足(Rachmalia et al. 2011)。相比之下,在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东北大地震中,尽管地震和海啸之间的时间很短,但当地紧急预警系统的有效性和日本公民的防灾准备挽救了许多生命。这些例子说明,个人防灾准备对于减轻灾害影响至关重要。为重大灾难做好准备是使受灾人口遭受的损失最小化的最有效方法(Banerjee和Gillespie 1994)。应急管理官员和灾害规划人员认识到,在地震或其他灾害发生后的最初72小时内,个人和家庭应做好自给自足的准备,因为服务和供应可能会中断,紧急援助可能无法立即获得(Russell等,1995年,Basolo等,2009年)。准备也与飓风期间的成功疏散有关(Howell和Bonner 2005年,Dash和Gladwin 2007年),也与个人应对创伤的复原力提高有关(Bravo等,1990年)。因此,美国政府将资源用于提高个人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应急准备(Eisenman et al. 2006)。
本文以2012年4月11日的印度洋地震为例,调查了生活在泰国攀牙省安达曼海岸的居民对紧急灾害准备的决定因素。4月11日的地震不仅引发了海啸警报,还引发了一系列较小的次生地震。这项调查是在印度洋地震发生后立即进行的,在小地震发生期间和之后不久进行的,这使我们能够在灾难准备受到事件考验的时刻观察防灾准备。我们分析了4月11日地震后海啸和地震的准备行动。特别是,我们调查了受教育程度与备灾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可能影响备灾行动的相关人口、社会经济和社区特征。我们研究了在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教育如何影响防灾准备,以及教育如何与其他特征相互作用,形成防灾准备行为。此外,鉴于社区中的人们相互作用和交换信息,我们认为生活在平均教育水平较高的社区有利于提高防范水平。
这项研究从三个方面补充了关于灾害准备和脆弱性的文献。首先,很少有研究关注教育程度与备灾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研究也没有深入考虑教育如何影响备灾。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探索正规教育如何影响准备行动的合理解释,扩展了当前的文献。第二,虽然大多数研究调查的是个人或家庭层面的教育对备灾的影响,但我们也考虑了社区层面的教育和人口因素的影响。第三,关于防灾的科学研究主要在美国进行。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很少(Mishra和Suar 2007, Mishra等人2010,Ferdinand等人2012)。我们提供了关于泰国的新的经验证据,那里的灾害准备工作尚未进行调查。
文献综述与假设
备灾行动受到广泛因素的影响。风险感知与灾害准备密切相关,因为个人必须感知到风险,才有动机启动准备行动(Sattler等人,2000年,Miceli等人,2008年)。个人先前在危险事件中的经历可以提高风险感知并促进防范行动(Russell et al. 1995, Lindell and Perry 2000, tekeli - yeil et al. 2010)。影响防范行为的其他因素因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而大不相同。不同社会群体的个体接受和评估风险信息不同,开展防范措施的资源也不平等。例如,有证据表明,妇女和男子采取的准备活动类型不同。虽然妇女比男子更有可能为家庭做好防灾准备,但她们在正式应急规划组织中的代表较少(Fothergill 1996年)。准备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Sattler et al. 2000, Mishra and Suar 2005),但非常老的人不太可能进行准备工作(Heller et al. 2005)。除了教育,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收入、住房所有权和在同一地点的居住时间也与灾害准备呈正相关(Lindell和Perry 2000, Eisenman等人2006,Reininger等人2013)。尽管与备灾相关的许多因素,如年龄、性别和种族,都属于由自然决定的特征,但收入和教育等特征则取决于个人的主动性,可以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实现。因为收入和教育与防灾准备呈正相关(Russell et al. 1995, Liu et al. 1996, Lindell and Perry 2000, Bourque et al. 2012),提高一个人的社会经济水平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增加防灾准备活动。我们认为,教育尤其是促进备灾的关键工具,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拥有更好的经济资源来开展备灾行动,而且因为教育可能影响认知要素,塑造个人感知和评估风险的方式,以及他们处理风险最小化信息的方式(Menard等,2011年)。
因为防范行动与个人对风险信息的感知和行动密切相关(Tierney et al. 2001),受过教育的个人可能有更多的风险意识,因为他们可能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并能够更好地评估风险信息(Jamison and Moock 1984, Rogers 1995, Asfaw and Admassie 2004)。还有证据表明,教育增加了对一般知识的获取,而这些知识可能影响价值观、优先事项、规划未来的能力以及适当分配现有资源的能力(Thomas等人,1991年;gllewwe, 1999年;Burchi, 2010年)。因此,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在灾难来临时可以派上用场。这导致了以下假设:
- H1:教育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对备灾产生正向影响,收入水平与备灾呈正相关。
- H2:教育对防灾有积极的直接影响,因为教育提高了认知和风险评估技能。
除了正规学校教育外,有证据表明,灾害教育干预措施可以对提高对灾害的认识和知识产生影响,从而可以加强备灾行动(Faupel和Styles 1993年,Tanaka 2005年,Page等人2008年)。正式学校教育与灾害教育干预措施之间的联系已得到承认,一些国际机构已将与灾害有关的教育作为建设抗灾社会的关键方法加以推广(国际减灾会议2007年,Selby和Kagawa 2012年)。然而,很少有实证研究考虑正规教育和灾害教育在形成备灾行为方面的相互作用。认为正规教育可以提高学习技能,这里提出的假设如下:
- H3:与灾害相关的教育增加了防灾准备,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中这种增加更大。
2012年印度洋地震案例研究
2012年印度洋地震
我们将2012年印度洋地震作为个人应急准备的案例研究。地震在泰国很罕见。在过去的40年里,该国只经历了8次中等地震(5.0 - 5.9级)(CICC 2012)。因此,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对地震的准备工作都没有得到优先重视。2012年印度洋地震之后,海啸警报和许多其他地震接踵而至。因此,地震使该地区的人们处于高度警惕状态,并可能在居民中引发了防范行动。2012年4月11日当地时间15时38分,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班达亚齐省西南434公里处发生8.6级强烈海底地震。随后在当地时间17:43向南200公里处又发生了一次8.2级的大地震,以及多次余震(USGS 2012)。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了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海啸警报,从澳大利亚、印度到遥远的非洲。在泰国,防灾和减灾部(DDPM)向南部六个省安达曼海岸的居民发布了海啸紧急警报和疏散令,2004年印度洋海啸也曾袭击过该地区。幸运的是,毁灭性的海啸没有发生,因为最初的地震和8.2级余震都是滑动走向地震,即两个构造板块——印度和澳大利亚板块——水平地相互滑动,这种横向运动没有导致水的垂直位移。几小时后,海啸警报被解除(BBC 2012)。
虽然没有发生海啸,但地震引发了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恐惧,尤其是在2004年海啸破坏的地区。5天后,即2012年4月16日,当地时间16:44,普吉岛发生4.3级地震,震中位于Thalang区,加剧了这种恐慌。随后,在2012年4月22日发生了一系列超过26次的余震。普吉岛地震可能是由印尼地震引发的,因为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4月11日之后的6天内,大地震的发生显著增加(Pollitz et al. 2012)。印尼和普吉岛的地震使安达曼南部海岸附近的居民处于高度警惕状态,因为他们担心余震和2004年海啸重演的威胁。
数据和方法
研究区域
我们选择攀牙省进行研究,是因为该省在2004年的海啸中遭受了最大的人员损失和巨大的经济影响。在受海啸(2010年Nidhiprabha)影响的泰国六个省中,海岸线240公里的攀牙一省就有5880人丧生,占泰国死亡和失踪人数总数的72%。Takua Pa区因其众多的海滩度假村而受到游客的欢迎,在2004年的灾难中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坡道高度在5至10米之间(粮农组织2005年,Römer等人,2012年)。在一些地区,淹没距离达到内陆两公里,造成了广泛的破坏(Thanawood et al. 2006)。考虑到2004年地震的大规模影响,攀牙居民可能会提高个人防灾措施。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评估了2012年4月11日由DDPM发布海啸警报的地区的灾害准备情况。随机选取了9个村庄作为访谈地点。这些村庄在人口数量和防灾水平方面差别很大(见图1)。
数据源
分析基于两个数据源。个人防范数据来自于2012年4月17日至5月13日期间,由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人口研究学院对位于梵雅省海啸高危地区的家庭进行的调查(见图1)。该调查包括由训练有素的访谈人员和当地研究人员用泰语进行的面对面访谈。采用系统随机抽样的方法,每村抽取30%的农户进行访谈。总共对563个家庭进行了访谈,首先与户主接触;如果不在场,则要求配偶或15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参加。问卷包含了受访者和家庭的基本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的问题。一系列与2012年印度洋地震的认识、反应和准备相关的问题也被包括在内。还询问了有关2004年海啸的经验、参与的社会活动和收到的信息渠道等问题。最终的样本包括557个对分析中使用的所有问题都有有效回答的家庭。村庄一级的基本人口和教育数据来自2010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由泰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汇总形式。
变量
根据以往文献中引用的与备灾行为相关的特征,实证分析探讨了备灾行动的决定因素。我们特别调查了正规教育和防灾准备之间的关系。因变量
在调查期间,由于印度尼西亚和随后的普吉岛地震,泰国南部的安达曼海岸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因此我们关注的结果是,生活在高危地区的人们是否采取了任何措施,为地震和可能随之而来的危险做好准备。因变量来自一个问题:“在2012年4月11日印尼地震后,你或你的家人是否采取了任何准备行动?”应答类别为:(1)无准备;(二)密切关注形势;(3)求生包的准备;(四)与家庭成员制定疏散程序和应急预案;(五)房屋结构检查;(6)其他准备。解释变量
1)教育:根据教育可以提高防灾意识的假设,我们在印度洋地震后从三个层面衡量了教育和防灾准备之间的关系。- 个人水平——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受访者分为四类:(1)未受教育和初等;(2)降低二次;(3)高中;和(4)三级
- 家庭水平-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家庭成员人数
- 村一级————村里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男子和妇女的比例
- 海啸经历-如受访者曾受2004年海啸影响,则编号1;0,否则
- 参加海啸演习和/或灾害教育-代码1(如被调查者曾参加海啸演习和/或灾害教育);0,否则
- 信息源数量-一个连续变量,衡量受访者获得2012年4月11日地震和海啸警报新闻的信息源数量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家庭、村庄人口统计和其他相关特征。- 个人水平——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在一所房子里居住的年限
- 家庭水平——家庭收入,常住人口数量,0-5岁成员数量,60岁以上成员数量,残疾成员数量,家庭是否位于沿海地区
- 村一级-村指标,妇女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
统计技术
为了调查个人准备的决定因素,我们进行了卡方分析,比较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进行的准备活动的数量。在决定因素为连续变量的情况下,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以比较相关变量按准备活动数量的平均数。随后,假设一个人的备灾结果很可能是个人和家庭特征的产物,以及此人所居住的村庄的特征,我们进行了多变量分析,以探索不同因素对备灾行动的同时影响。
由于结果变量(准备措施的数量)不是正态分布,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不能使用,因为正态性假设将被违反。然后我们将准备活动的数量按顺序分为三个类别:不准备、一个准备措施、两个或两个以上准备措施。尽管有序逻辑回归是一种适合于顺序响应变量的方法,但该模型仅对满足比例比值假设的数据有效,即描述任意两对结果组之间关系的系数在统计上相同。对于我们的数据,似然比检验表明比例优势假设被违反了(Wolfe and Gould 1998)。因此,我们决定采用部分比例比值模型,该模型允许违反比例比值假设的系数在逻辑方程中变化,即对因变量有不同的影响(Peterson and Harrell 1990, Fullerton and Xu 2012)。
部分比例优势模型(PPOM)可以表示为广义有序logit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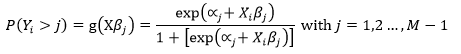 |
(1) |
在哪里米序数因变量(在我们的例子中是3)的类别数和β j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j对于违反比例优势假设的系数β j=β.对于我们的分析,M = 3,因此PPOM相当于一系列的二元逻辑回归,其中因变量的类别是组合的。因变量随着所采取的准备措施的增加而定义:Y= 1表示没有准备,Y= 2表示采取了一次准备措施,且Y采取两种或两种以上准备措施= 3。在我们的例子中,米= 3,则forJ= 1类日元是与Y2而且Y3(分对数1);和J= 2的对比是日元而且Y2与Y3(logit 2)。这样,每一组与准备措施数量较多的组进行比较。
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在统计软件STATA,版本11中进行的,使用PPOM进行估计gologit2,一个用户编写的程序(Williams 2006)。
结果
防灾准备与个人、家庭和村庄特征的二元关系
表1描述了样本在个人、家庭和村庄层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这些特征与防范措施数量之间的二元关系也被提出。如表1所示,根据年龄和职业的不同,开展的防范行动数量有显著差异:最年轻年龄组的28.6%、最年长年龄组的34.7%和从事农业的44%的人没有采取任何防范行动。与灾害有关的变量与备灾有显著的关联。受2004年海啸影响并参加过疏散演习和灾害教育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做好准备,更有可能采取不止一项准备措施。拥有更多海啸和地震信息来源的个人也更有可能做好准备。考虑到家庭特征,家庭中的人口构成与防灾准备有关,因此,年龄≥60岁成员人数较多(0.72)和残疾成员人数较少(0.02)的家庭不太可能做好防灾准备。请注意,在大多数家庭中,老年人和残疾人家庭成员的平均人数不到1人。准备工作与家庭位置显著相关:只有14.3%的生活在海岸的人没有准备工作,相比之下,居住在距离海岸≥1公里的人有38.9%没有准备工作。就村庄特点而言,居住在妇女比例较高的村庄的受访者采取防范行动的比率较低。
关于备灾和教育,个人教育与所采取的备灾措施数量之间的关系很弱。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准备的可能性较低(29.4%)。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做好准备,并采取了不止一次的准备行动(41.2%)。村庄的平均教育水平也与备灾能力高度相关,备灾活动数量较高的受访者更有可能生活在男女至少接受中等教育比例较高的村庄。
考虑村庄影响的防灾准备
在表2中,考虑到村庄之间的差异,我们应用部分比例优势模型(PPOM)来估计与备灾相关的因素。模型1和2包括一个村庄指标变量,以控制备灾结果可能因居住的村庄而不同的可能性。在模型3中,我们探讨了村庄人口特征与防灾准备之间的关系。请注意,村庄指标没有包括在模型3中,因为带有村庄指标的模型相当于固定效应估计器,其中村庄级协变量被视为干扰,无法估计(Paul等人,2010年)。我们还排除了原始样本中所有受访者都已采取准备行动的两个村庄(见图1)。因此,表2和表3中的分析包括544名受试者的样本。
我们对参数估计的解释如下。结果可以用与传统的有序logit模型相同的方式来解释,即响应变量的对数概率的变化,每单位变化在预测器中。表2和表3给出了比值比(OR)的结果,回归系数(exp)的指数函数β).OR > 1表示较高的准备概率,而OR < 1表示较低的准备概率。与有序logit模型不同的是,在PPOM中,对违反比例优势假设的每个变量估计多个系数。因此,对于这些变量,列出了两个不同的系数。第一个系数(不加粗)预测第一个logit方程(logit 1)的响应,而第二个系数(加粗)预测第二个logit方程(logit 2)的响应。在logit 1中,参考组没有准备;而在Logit 2中,参照组是没有做任何准备或只采取了一项准备措施的个人。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概率变化百分比用公式计算β1)。
表2中的模型估计值是逐步向前提出的。模型1调查了包括灾害相关变量在内的个别人口特征与灾害准备之间的关系。个人教育和婚姻状况似乎是备灾的关键决定因素。一般来说,较高的教育水平与较多的备灾活动密切相关。同样,已婚人士更有可能做好准备。在与灾害相关的变量方面,与我们在二元统计中发现的不同,2004年海啸的经历和参与疏散演习和灾害教育与灾害准备没有显著关联。信息来源的数量与所采取的防备行动的数量呈正相关。每增加一个信息源,准备的几率就增加1.35倍。模型2包括家庭特征。家庭收入与防灾准备没有显著关系。 Consistent with the binary statistics,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members aged ≥ 60 years, the lower the likelihood of preparation, but this applies only to the first logit equation. Likewise,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disabled members, the greater the odds of preparedness. We find a weak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of household members and the number of preparedness activities taken. Model 3 includes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model, the coefficients for education of household members becom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t is also found that while 1%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 a village reduces the likelihood of preparation by 17%, a 1%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with at least secondary education increases the odds of preparation by 11%.
个人教育和以往海啸经验对备灾决定因素的影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比较备灾决定因素的影响是否因个人教育和海啸经验而异。在表3中,我们估计了PPOM模型将样本分为:(1)个人教育,定义为中等教育以下的个人和中等教育以上的个人;(2)个人海啸经历,定义为未受2004年海啸影响的个人和受2004年海啸影响的个人。按个人教育程度划分样本,表3显示,准备可能性的预测因素因教育水平而有很大差异。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受访者来说,影响备灾的主要因素是信息来源的数量和一些家庭人口特征,即老年和残疾成员的数量。另一方面,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来说,显然,他们采取准备行动的可能性随着海啸经验、参与疏散演习、灾害教育和收到的信息来源的数量而增加。对于这一群体,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家庭成员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了准备的可能性。对于生活在一个家庭中,有一个、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分别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参加预科活动的几率显著增加2.5倍和4.5倍。关于根据海啸经历划分样本的分析,表3报告说,对于没有受到2004年海啸影响的个人,家庭成员的教育显然是采取准备行动的关键驱动因素。就这一群体而言,那些生活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家庭中的人,其准备的几率是那些生活在家庭成员都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家庭中的人的6.6倍。此外,中等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也比没有受过教育或只有初级教育水平的人有更大的准备倾向。同样地,准备的可能性随着这一群体信息来源的数量而显著增加。对于受2004年海啸影响的个人来说,准备的可能性与婚姻状况和家庭特征显著相关。离婚/分居/丧偶和已婚人士采取准备行动的几率是单身人士的6倍和8倍。尽管家庭中老年人的数量(仅适用于Logit 1)降低了准备活动的可能性,但残疾成员的数量增加了进行准备活动的倾向。
讨论
我们的多元估计显示,正规教育与个人、家庭和村庄层面的防范行动呈正相关。我们发现,在控制家庭收入后,个人和家庭教育水平的积极作用仍然存在。这表明,教育在提高防范能力方面独立于收入。因此,假设1,即教育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来提高防灾能力,是不被支持的。随后,很少有证据表明教育可能提高认知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因为研究发现,受到2004年海啸的影响增加了准备的可能性,但这只适用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成功地将他们以前的灾难经验转化为备灾行动。因此,假设2得到了部分支持。正如假设3所预测的那样,我们还观察到个人教育程度和防灾非正式教育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互作用。参加疏散演习和灾害教育可增加采取防备行动的可能性,但这只适用于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应答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更好的学习技能,也更善于处理抽象思维,例如,在像海啸演习这样的假设情况下。
除了个人教育的效果外,我们发现家庭成员的教育提高了防灾能力,特别是在没有受到2004年海啸影响的个人中。尽管灾害经验可以提高灾害意识,从而提高防灾行动(Russell et al. 1995, Sattler et al. 2000, Horney et al. 2008, tekeli - yeil et al. 2010),但那些没有这种经验的人可能难以感知与特定自然灾害相关的风险。然而,我们的结果表明,对于那些以前没有海啸经验的人来说,家庭成员的教育以及信息来源的数量是推动防灾准备的关键因素。因为信息是经过多个阶段处理的,包括听到信息、理解信息和感知其相关性(Nigg 1982年),教育可以塑造个人准确感知和评估风险的程度,并做出采取防范行动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可以提高风险意识,而不必直接经历自然灾害。
我们还发现个体的防灾准备因村庄的人口和教育构成而不同。一般而言,村内女性人口比例越大,个人的防灾准备水平越低。另一方面,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妇女比例越大,采取防范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社区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个人的应急准备行为?一种解释是,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拥有更紧密的社会关系,包括更高比例的亲属和邻居(Moore 1990, Renzulli et al. 2000),因此她们可能更有可能交换信息和相互帮助。然而,妇女通常拥有较少的社会经济资源,很少有机会加入正式的应急规划组织(Fothergill 1996年)。一个女性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的社区,由于女性获取信息渠道较少(Katungi et al. 2008),因此无法分享有用的信息,因此防灾准备可能较差。然而,生活在高学历妇女比例较高的社区可以提高个人的防灾能力,因为教育可以增加获得与灾害有关的信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机会。因此,社区中其他成员的防灾准备工作可以从这种女性社交网络中受益。
研究发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灾害的准备工作也在增加,这一发现与亚洲其他关注其他类型灾害后果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早期研究发现,尼泊尔教育水平较高的社区因洪水和滑坡而造成的人和动物死亡较少(K.C. 2013年)。同样,据报道,印度尼西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更好地应对海啸后的灾难阶段,特别是从长期来看(Frankenberg et al. 2013)。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可以成为减少亚洲环境危害脆弱性的重要资源。
尽管在本文中,我们提供了教育在加强灾害准备方面作用的证据,并调查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如何与灾害经验相互作用,但确定正规教育如何通过其他因素(如本研究未观察到的风险感知)增加备灾活动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防范行动既与对风险的认知有关,也与个人采取保护行动和应对的能力有关(Slovic 2000年)。对风险的看法因过去的灾害经历以及人口和社会经济概况而有很大差异。在防灾准备方面的教育差异可能部分是因为受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体根据其认知能力以不同的方式感知风险。同样,正规教育可能转化为更好地理解灾害教育的能力。为了加深我们对正规教育在备灾方面的作用的理解,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进行定性研究。
目前的研究并非没有局限性。首先,该研究可能存在从海啸风险地区向外迁移具有某些特征的个人或家庭的选择偏差。然而,就泰国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发生了海啸影响人口的大规模外逃(Naik et al. 2007)。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选择问题似乎是最小的。其次,受访者有可能误报他们的准备行动。他们可能会因为社会愿望偏见而过度报告他们的疏散计划或准备工具,因为受访者希望被面试官看得更好,或者觉得有义务报告他们准备了应对地震的计划或工具。同样,由于回忆偏差,也有可能少报灾害准备情况,尽管大多数采访是在地震后不久进行的。由于该研究没有其他来源的准备情况信息,这里提供的数据仅依赖于受访者的账户和报告行为。最后,数据不能让我们确定谁在一个家庭中实际启动了应急准备行动,因为调查只访问了每个家庭的一个受访者。因此,我们在分析中控制被调查者是否为一家之主,作为决策权力的代理。 A future study should attempt to identify who actually implemented preparedness measures in a household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disaster preparedness.
结论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提供的证据表明,在个人、家庭和村庄层面衡量的教育与防灾准备有显著关系。我们区分了正规学校教育和与灾害相关的培训对防灾行动的影响,发现灾害教育尤其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参与者中是有效的。正规教育可以增强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学习技能,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困难时期(比如灾难来袭时)能做出更好的反应。事实上,在过去没有灾难经历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家庭成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对灾难的准备更充分。教育也有溢出效应,这可能是通过村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来实现的,研究发现,生活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成员比例较高的村庄,与个人和家庭一级的防范活动数量呈正相关。我们的研究表明,与灾害相关的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准备能力,这对减轻灾害风险至关重要。然而,这种教育的效果可能只局限于人口的一个小群体,例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此,确保至少在中学一级普及正规教育的政策可以有助于减少脆弱性和减轻灾害影响。
致谢
这项工作的资金由欧洲研究理事会高级赠款、预测学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赠款协议ERC-2008-AdG 230195-FutureSoc)和chchadaphiseksomphot捐赠基金提供,用于“了解应对和适应极端气候事件的社会障碍”项目(赠款协议编号:RES560530150-beplay竞技CC)。作者要感谢Rugsapong Sanitya组织和准备调查数据,感谢Thana-on Punkasem协助制作攀牙地图。
文献引用
阿斯faw, A.和A. Admassie. 2004。教育对埃塞俄比亚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化肥使用的作用。农业经济学30:215 - 228。贝克,2011。佛罗里达家庭为飓风后的准备工作。应用地理31:46-52。http://dx.doi.org/10.1016/j.apgeog.2010.05.002
班纳吉,M. M.和D. F.吉莱斯皮,1994。战略和组织灾难准备。灾害18:344 - 354。http://dx.doi.org/10.1111/j.1467-7717.1994.tb00321.x
巴索洛,L. J.斯坦伯格,R. J.伯比,J.莱文,A. M.克鲁兹和C.黄。2009。对政府和信息的信心对感知和实际防灾准备的影响。环境和行为41:338 - 364。http://dx.doi.org/10.1177/0013916508317222
布尔克,L. B., D. S.米莱蒂,M.卡诺,M. M.伍德。2012。谁为恐怖主义做准备?环境和行为44:374 - 409。http://dx.doi.org/10.1177/0013916510390318
Bravo, M., M. Rubio-Stipec, G. J. Canino, M. A. Woodbury, J. C. Ribera. 1990。对灾难应激的心理后遗症进行前瞻性和回顾性的评估。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18:661 - 680。http://dx.doi.org/10.1007/BF00931236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2.亚齐地震后印度洋海啸警报解除。英国广播公司。(在线)网址: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7675399
Burchi, f . 2010。2003年莫桑比克儿童营养:母亲教育和营养知识的作用。经济学与人类生物学8:331 - 345。http://dx.doi.org/10.1016/j.ehb.2010.05.010
楚拉国际传播中心(CICC), 2012。泰国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中金公司,泰国曼谷。(在线)网址:http://www.cicc.chula.ac.th/en/2012-04-26-04-31-26/203-likelihood-of-earthquakes-in-thailand.html
N.达什和H.格拉德温。2007。疏散决策和行为反应:个人和家庭。自然灾害评估8:69 - 77。http://dx.doi.org/10.1061/(第3期)1527 - 6988(2007)八3 (69)
爱德华,M. L. 1993。社会位置和自我保护行为:对地震准备的启示。大规模紧急情况和灾害国际杂志11:293 - 303。
艾森曼,D. P., C.沃尔德,J.菲尔丁,A.朗,C.塞托吉,S.希基,L.盖尔伯格。2006。洛杉矶县个人层面的恐怖主义防范差异。美国预防医学杂志30:1-6。http://dx.doi.org/10.1016/j.amepre.2005.09.001
福佩尔,c.e, S. P.凯利和T.皮特,1992。灾害教育对家庭防备雨果飓风的影响。大规模紧急情况和灾害国际杂志10:5-24。
福佩尔和斯泰尔斯1993。飓风雨果后的灾害教育、家庭准备和压力应对。环境和行为25:228 - 249。http://dx.doi.org/10.1177/0013916593252004
费迪南,I., G. O 'Brien, P. O 'Keefe, J. Jayawickrama. 2012。贫困和减少社区灾害风险的双重束缚:来自加勒比地区的案例研究。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杂志2:84 - 94。http://dx.doi.org/10.1016/j.ijdrr.2012.09.003
联合国粮农组织(粮农组织)。2005.粮农组织/MOAC联合技术损失和需求评估团对泰国海啸受灾六省渔业和农业部门的详细技术损失和需求评估报告.粮农组织,泰国曼谷。
Fothergill, a . 1996。性别、风险和灾难。大规模紧急情况和灾害国际杂志14:33-56。
Frankenberg, E., B. Sikoki, C. Sumantri, W. Suriastini和D. Thomas. 2013。自然灾害后的教育、脆弱性和复原力。生态和社会18(2): 16。http://dx.doi.org/10.5751/ES-05377-180216
富勒顿,a.s.,徐杰。2012。顺序响应变量的比例比与部分比例约束模型。社会科学研究41:182 - 198。http://dx.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11.09.003
Glewwe, p . 1999。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母亲的教育提高了儿童的健康?来自摩洛哥的证据。人力资源杂志3:124 - 159http://dx.doi.org/10.2307/146305
海勒,K., D. B.亚历山大,M.盖兹,B. G.奈特,T.罗斯,2005。社会和个人因素作为地震准备的预测因素:支持提供的作用、网络讨论、负面影响、年龄和教育。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35:399 - 422。http://dx.doi.org/10.1111/j.1559-1816.2005.tb02127.x
霍尼,J., C.斯奈德,S.马龙,L.甘蒙斯,S.拉姆齐。2008。与飓风防备有关的因素:飓风前评估的结果。灾害研究杂志3:143 - 149。
Howell, S. E.和D. E. Bonner, 2005。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的飓风疏散行为:12个教区调查.新奥尔良大学,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杰克逊,1981年。对地震危险的反应:北美西海岸。环境和行为13:387 - 416。http://dx.doi.org/10.1177/0013916581134001
贾米森,D. T.和P. R.穆克,1984。尼泊尔农民教育和农业效率:学校教育、推广服务和认知技能的作用。世界发展12:67 - 86。http://dx.doi.org/10.1016/0305 - 750 x (84) 90036 - 6
卡通吉,S. Edmeades和M. Smale, 2008。乌干达农村的性别、社会资本与信息交换。国际发展杂志20:35-52。http://dx.doi.org/10.1002/jid.1426
k.c., s . 2013。尼泊尔社区对洪水和山体滑坡的脆弱性。生态和社会18(1): 8。
金,研究。康j ., 2010。沟通,邻里归属感和家庭飓风防备。灾害34:470 - 488。http://dx.doi.org/10.1111/j.1467-7717.2009.01138.x
科恩,S., J. L.伊顿,S.费罗兹,A. A.班布里奇,J.胡拉坎,和D. J.巴奈特。2012。个人灾难准备:文献综合综述。灾害医学和公共卫生防备6:217 - 231。http://dx.doi.org/10.1001/dmp.2012.47
莱曼,D. R.和S. E.泰勒,1987。与地震的约会:应对可能发生的、不可预测的灾难。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13:546 - 555。http://dx.doi.org/10.1177/0146167287134011
林德尔,M. K.和R. W.佩里,2000。家庭调整对地震危害的影响:研究综述。环境和行为32:461 - 501。http://dx.doi.org/10.1177/00139160021972621
刘s, L. E. Quenemoen, J. Malilay, E. Noji, T.申斯,J. Mendlein. 1996。对恶劣天气预警系统和灾害准备的评估,阿拉巴马州卡尔霍恩县,1994年。美国公共卫生杂志86:87 - 89。http://dx.doi.org/10.2105/AJPH.86.1.87
梅纳德,洛杉矶,R. O.斯莱特,J.弗莱茨,2011。备灾和教育成就。应急管理杂志9:45-52。
米塞利,R., I. Sotgiu和M. Settanni, 2008。灾害准备和感知洪水风险:一项在意大利高山山谷的研究。环境心理学杂志28:164 - 173。http://dx.doi.org/10.1016/j.jenvp.2007.10.006
米莱蒂,D. S.和C.菲茨帕特里克,1992。帕克菲尔德地震预测实验中风险沟通的因果序列。风险分析12:393 - 400。http://dx.doi.org/10.1111/j.1539-6924.1992.tb00691.x
Mishra, S. Mazumdar, D. Suar. 2010。放置附件和防洪准备。环境心理学杂志30:187 - 197。http://dx.doi.org/10.1016/j.jenvp.2009.11.005
Mishra, S.和D. Suar. 2005。年龄、家庭和收入影响备灾行为。心理研究50:322 - 326。
Mishra, S.和D. Suar. 2007。人们吸取的教训是否决定了对灾害的认知和防备?心理学与发展中的社会19:143 - 159。http://dx.doi.org/10.1177/097133360701900201
摩尔,g . 1990。男性和女性个人网络的结构决定因素。美国社会学评论55:726 - 735。http://dx.doi.org/10.2307/2095868
墨菲,s.t, M.科迪,L. B.弗兰克,D.格利克和A.昂。2009。应急准备和遵守情况的预测因素。灾害医学和公共卫生防备.
奈克,A., E.斯蒂格,和F.拉茨科。2007。移徙、发展与自然灾害:来自印度洋海啸的见解。移徙组织移徙研究系列,国际移徙组织,瑞士日内瓦。
Nidhiprabha, b . 2010。泰国。171 - 224页在S.贾亚苏里亚和P.麦考利,编辑。亚洲海啸:灾后援助与重建.亚洲开发银行学院和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切尔滕纳姆,英国。
尼格,1982年。不确定条件下的通信:了解地震预报。《通信32:27-36。http://dx.doi.org/10.1111/j.1460-2466.1982.tb00474.x
诺里斯,F. H.史密斯和K.卡尼亚提,1999。回顾经验-行为假说:飓风雨果对灾害准备和其他自我保护行为的影响。基础与应用社会心理学21:37-47。
佩奇,L., J.鲁宾,R. Amlôt, J.辛普森,S.威斯利,2008。伦敦人准备好应对紧急情况了吗?伦敦爆炸案后的一项纵向研究。生物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6:309 - 319。http://dx.doi.org/10.1089/bsp.2008.0043
保罗,C., C.克莱尔,S.菲奥娜,V.安娜。2010。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教育研究的一些考虑.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经济系。
彼得森,B.和F. E.哈勒尔,Jr. 1990。顺序响应变量的部分比例比值模型。应用统计学39:205 - 217。http://dx.doi.org/10.2307/2347760
波利茨、F. F.、R. S.斯坦、V.塞维尔根和R. Bürgmann。2012.2012年4月11日东印度洋地震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余震。自然490:250 - 253。http://dx.doi.org/10.1038/nature11504
Rachmalia, U. Hatthakit和A. Chaowalit. 2011。生活在受影响地区和未受影响地区的人们的海啸防备:印度尼西亚亚齐沿海地区的一项比较研究。澳大利亚急救护理杂志14:17-25。http://dx.doi.org/10.1016/j.aenj.2010.10.006
拉米雷兹,M和c。2005.地震创伤流行病学研究。流行病学评论27:47-55。http://dx.doi.org/10.1093/epirev/mxi005
莱宁格,B. M., M. H. Rahbar, M. Lee, Z. Chen, S. R. Alam, J. Pope, B. Adams. 2013。灾害易发地区低收入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社会资本和防灾准备。社会科学与医学83:50-60。http://dx.doi.org/10.1016/j.socscimed.2013.01.037
伦祖利,洛杉矶,H.奥尔德里奇和J.穆迪,2000。家庭问题:性别、网络和创业成果。社会力量79:523 - 546。http://dx.doi.org/10.1093/sf/79.2.523
罗杰斯,E. M. 1995。创新的扩散.第四版。美国纽约自由出版社。
Römer, H., P. Willroth, G. Kaiser, A. T. Vafeidis, R. Ludwig, H. Sterr,和J. Revilla Diez. 2012。遥感技术在海啸危害和脆弱性分析方面的潜力——泰国攀雅省的一个案例研究。自然灾害与地球系统科学12:2103 - 2126。http://dx.doi.org/10.5194/nhess-12-2103-2012
罗素,J. D.戈尔茨,L. B.布尔克,1995。两次地震前后的准备和减灾行动。环境和行为27:744 - 770。http://dx.doi.org/10.1177/0013916595276002
萨特勒,C. F.凯泽,J. B.希特纳,2000。灾难准备:先前的经验、个人特征和灾难之间的关系。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30:1396 - 1420。http://dx.doi.org/10.1111/j.1559-1816.2000.tb02527.x
Selby, D.和F. Kagawa. 2012。在学校课程中减少灾害风险:来自30个国家的案例研究.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瑞士日内瓦。
西格尔,J. M.肖夫,A. A.阿菲,L. B.布尔克,2003。从两场灾难中幸存下来:对第一场灾难的反应能预测对第二场灾难的反应吗?环境和行为35:637 - 654。http://dx.doi.org/10.1177/0013916503254754
Slovic, p . 2000。对风险的感知.趋势,伦敦,英国。
斯皮塔尔,M. J.麦克卢尔,R. J.西格特,F. H.沃尔基。2008。预测两种类型的地震准备:生存活动和减灾活动。环境和行为40:798 - 817。http://dx.doi.org/10.1177/0013916507309864
田中,k . 2005。灾害教育对公众准备和减轻地震灾害的影响:日本福井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的跨国比较。应用地理25:201 - 225。http://dx.doi.org/10.1016/j.apgeog.2005.07.001
tekeli - yeil, S, N. Dedeoǧlu, M. Tanner, C. brun - fahrlaender,和B. Obrist. 2010。伊斯坦布尔预测地震的个人准备和减灾行动。灾害34:910 - 930。http://dx.doi.org/10.1111/j.1467-7717.2010.01175.x
Thanawood, C. Yongchalermchai,和O. Densrisereekul. 2006。2004年12月泰国南部海啸的影响和灾害管理。海啸危害科学24:206 - 217。
托马斯,J.施特劳斯和m . h。戴安娜》1991。母亲的教育如何影响孩子的身高?人力资源杂志26:183 - 211http://dx.doi.org/10.2307/145920
蒂尔尼,K. J.林德尔,R. W.佩里,2001。面对危险和灾难:理解人的维度.约瑟夫·亨利出版社,美国华盛顿特区。
特纳,R. H., J. M.尼格,D. H.帕斯,1986。等待灾难:加利福尼亚的地震监测.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加州,美国。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减灾战略)。2007.2005-2015兵库行动框架:建设国家和社区抵御灾害的能力.减灾,瑞士日内瓦。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12.8.6级-苏门答腊岛北部西海岸。美国弗吉尼亚州莱斯顿USGS。(在线)网址:http://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eqinthenews/2012/usc000905e/
威廉姆斯,r . 2006。序因变量的广义有序logit/部分比例比值模型。占据杂志58 - 82。
沃尔夫,R.和W.古尔德,1998。序数响应模型的近似似然比检验。占据技术通报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