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pdf本文的版本
D - az-Reviriego, I. L. Gonz - lez-Segura,Fern ? ndez-Llamazares, P. L. Howard, J. Molina,和V. Reyes-Garc ?2016.社会组织影响着亚马逊地区家庭花园药用植物的交换和物种丰富度。生态和社会21(1): 1。
http://dx.doi.org/10.5751/ES-07944-210101
社会组织影响着亚马逊地区家庭花园药用植物的交换和物种丰富度
摘要
药用植物为世界各地的土著和农民社区提供了满足其保健需求的手段。家庭菜园通常充当药柜,为家庭需求提供容易获得的药用植物。社会结构和社会交流被认为是影响人们在其家园中维持的物种多样性的因素。在此,我们评估了药用知识和植物材料的交流与家庭花园药用植物丰富度之间的关系。以提斯曼的亚马逊家园为例,我们探讨了社会组织是否塑造了药用植物知识和药用植物材料的交流。我们还使用网络中心性度量来评估人们在药用植物知识和植物材料交换网络中的位置和表现。结果表明,社会组织,特别是亲属关系和性别关系,对药用植物交换模式有显著影响。家庭园林植物总丰富度和药用植物物种丰富度与园丁在网络中的中心性有关,中心性越高的人保持的植物丰富度越高。因此,与农业生态条件、园丁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文化社会结构一起,似乎是家庭花园植物丰富度的重要决定因素。了解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热带家庭菜园的一般物种多样性,特别是药用植物多样性,可以帮助决策者、卫生提供者和当地社区更好地了解如何促进和保护就地药用植物。 Biocultural approaches that are also gender sensitive offer a culturally appropriate means to reduce the global and local loss of both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介绍
药用植物为缺乏生物医学医疗系统的人提供了当地可获得的、文化上合适的、经济上可负担的医疗保健选择。事实上,大多数土著和农民社区通过使用药用植物来满足其初级保健需求。虽然一些药用植物来自野生,但也有许多来自农田和家庭花园,既供家庭消费,也供销售(例如,Bernholt等人2009年,Aceituno-Mata 2010年,Thomas和van Damme 2010年,Yang等人2014年)。特别是,热带家庭花园支持高度的物种多样性,并帮助社区满足卫生需求,构成就地种质库、生物多样性库和药箱(Finerman和Sackett 2003年,Huai和Hamilton 2009年)。
多样性homegardens
热带家庭花园以其典型的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而闻名。这种物种多样性是园丁精心选择和管理的结果,目的是提供他们认为对生存和生计重要的产品(Kumar和Nair, 2006年)。家庭花园的多样性部分取决于气候条件、海拔、花园的大小和年龄、远离城市中心和村庄的大小,以及其他因素(Wezel and Bender 2003, Kehlenbeck and Maass 2004, Wezel and Ohl 2005, Rao and Rajeswara Rao 2006)。此外,园丁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征对解释家庭花园的植物多样性也很重要。例如,Howard(2006)表明,在拉丁美洲的家庭菜园中,劳动分工、知识、对花园资源的获取和商品化程度有助于解释家庭菜园的结构、组成和功能。园丁的性别和园艺任务的性别分布与伊比利亚半岛家庭花园的多样性有关(Reyes-García et al. 2010),在那里,尽管规模较小,离住所更近,但与主要由男性管理的花园相比,主要由女性管理的花园单位面积的物种多样性更大。在秘鲁亚马逊花园中,在物种丰富度、家庭花园组成和药用植物存在方面,家庭花园多样性的差异与种族(乌拉尼娜、混血和阿丘阿尔)有关;一些药用物种是由一个或另一个伦理群体专门栽培的(Perrault-Archambault和Coomes 2008)。Finerman和Sackett(2003年)观察到,在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花园由妇女管理,主要用于药用植物生产,物种组成反映了家庭人口统计数据(如年龄、组成)和生命周期阶段(如生殖状况),以及家庭中个人的具体健康需求。
菜园多样性还受到种植材料的获取和交换的强烈影响,如种子、木桩、茎和插枝(aguilar - st - øen等,2009年,Coomes 2010年),这些对发展和保持植物多样性至关重要。人们的迁移和迁移模式通常伴随着种子和植物的流动,这改变、丰富和多样化了移民的家园花园(Voeks 2004年,Kujawska和Pardo-de-Santayana 2015年)。例如,Lerch(1999)在一项关于秘鲁亚马逊土著人民种植材料交换网络的研究中发现,家庭花园的植物多样性与家庭植物交换频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an和Coomes(2004)在同一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然而,家居种植材料的交换通常包含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大多数交流发生在亲属、亲戚、密友和邻居之间(Aguilar-Støen et al. 2009, Buchmann 2009),并且主要发生在女性之间(Boster 1985, Sereni Murrieta和Winklerprins 2003, Lope-Alzina和Howard 2012)。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引导社会交流
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来调查家居产品(商品和种植材料)和相关知识的交换。Calvet-Mir等人(2012)探索了加泰罗尼亚比利牛斯山脉家庭菜园的种子交换网络,并评估了其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他们发现,在种子交换网络中被提及次数更多、具有较高中介水平的人比在网络中不那么中心的人保存了更多的本地品种,对这些品种有更多的知识。在伊比利亚半岛园丁的一项类似研究中,Reyes-García等人(2013)发现,个体在种质交换网络中的接触数量与他们的农业生态知识呈正相关。Lope-Alzina(2014)报告称,在墨西哥尤卡蒂克-玛雅社区的成员中,菜园是交换种植材料的主要来源。作者发现,尽管市场参与度很高,但送礼仍然是主要的交换形式,大多数礼物来自家庭花园,大多数交换发生在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网络中的女性之间。在自己的亲属网络中,处于等级顶端的老年女性是最杰出的捐赠者。
社会网络分析也被用来探索药用植物知识的传播途径。例如,霍普金斯(2011)对墨西哥尤卡特克-玛雅人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对草药的知识与此人在草药治疗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呈正相关。其他研究人员通过社会网络模型评估了文化传播途径中的选择性学习偏差。Henrich和Broesch(2011)询问斐济村民,如果他们对如何使用药用植物有疑问,他们会向谁寻求建议;他们的结果表明,知识渊博、年龄较大、女性以及缺乏正规教育的人被选为学习药用植物的榜样的机会增加了。综上所述,先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与药用植物知识有关,亲属关系、性别和文化学习途径塑造了社会网络。
在这里,我们试图通过评估通过社会网络交换药用知识和植物材料对提斯曼亚马逊自家花园药用植物多样性的影响,为这些研究方向做出贡献。我们探讨了社会组织(即亲属关系、性别关系和园艺中的劳动和任务分工)是否促进了药用植物知识和药用植物材料的交换。我们使用网络中心性度量来评估人们在知识和植物物质交换网络中的位置和表现,假设在知识或植物物质交换网络中中心性越高的人保持其家园药用植物多样性越高。
方法
我们的研究是在玻利维亚贝尼省亚马逊低地森林的提斯曼的觅食园艺学家中进行的。我们选择了位于曼尼基河沿岸的两个村庄,在提斯曼人的土著领土内。虽然这两个村庄相对孤立和自给自足,但它们的孤立程度不同。一个村庄离集镇更近(独木舟旅行一天就可以到达),而另一个村庄更偏远(独木舟旅行三天就可以到达;图1)。
提斯曼纳村庄的社会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大多数提斯曼纳人实行跨表亲婚姻(Daillant 2003年),居住通常是母系亲属制(夫妇与妻子的父母住在一起或附近)。传统上,提斯曼人的半游牧定居点很小,由两到三个大家庭组成,通常相距很远(Chiccón 1992, Ellis 1996)。新教传教士的影响和20世纪中期正规教育的引入促进了不同宗族或群体在学校周围的定居和融合。如今,提斯曼人仍然非常频繁地更换住处,甚至是在村庄里,在收获季节搬到离农田更近的地方,在鱼充足的旱季搬到河边。
在这些村庄,生计大多以自给自足为导向,依赖于觅食和瑞典农业。除了在远离家庭的不同距离处有坡度的地块外,提斯曼夫妇还在自家花园中培育和管理着各种各样的物种。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来定义家庭花园(例如,Kumar和Nair 2006),但我们使用的概念与提斯曼人实践的土地使用类型非常一致:“属于家庭成员种植和/或照料有用植物的家庭周边区域”(Perrault-Archambault和Coomes 2008)。经常使用或常见的药用植物与果树、棉花和辣椒一起在家庭花园中发现(Reyes-García et al. 2003, 2005)。
由于获得生物医学保健的机会非常有限,药用植物为提斯曼人提供了当地可获得的和与社会文化相关的治疗健康问题的选择。疾病首先在家庭中治疗,妇女是主要治疗者(Chiccón 1992)。然而,无论男女,都在房子周围种植植物。非常有趣的是,提斯曼人承认这些药用植物的习惯所有权,并对这种权利有详细的了解(另见Howard and Nabanoga 2007)。在提斯曼人习惯的用益权保有制度中,花园属于最初建立它们的家庭(例如,以前的居民)。被遗弃的花园通常被以前遗弃它的家庭或他们的近亲重新占用,他们从以前的居住者那里获得使用它们的许可(Piland 2000)。当一个家庭成员去世时,为了摆脱坏灵魂和避免死者的灵魂拜访,提马尼人会搬到另一个地方(Chicchón 1992);剩下的花园完好无损(Piland 2000)。
数据收集
第一和第三位作者在该地区生活了18个月(2012年1月- 2013年11月),让他们在园艺时积极观察、参与并与提斯曼人互动。对一些线人执行了不同的任务;例如,我们陪着他们从他们的花园收集产品,帮助他们种植和除草。
在2012年8月至12月期间,对由户主种植或管理的所有家庭花园里的植物进行了个人盘点。共采访了86名信息提供者(46名女性和40名男性),约占所有户主的80%。其中55人住在离城镇较近的村庄,31人住在较偏僻的村庄。每个告密者都被要求单独展示花园中种植的植物,并提供它们的方言或常用名称和用途。用途分为四类:食品、医药、手工(包括用于制作袋子、地毯和弓箭的植物)和其他(包括鱼中毒、观赏性和建筑用途)。一种植物可以分为多个类别(例如,一种植物既可食用又可药用)。当举报人指出一种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时,他们会被问及它用来治疗的疾病。
社交网络数据是通过个人访谈收集的。我们使用召回方法,使用一组名称生成器来收集与知识(例如,关于药用植物的信息和建议)和植物材料(繁殖体、种子、植物)交换(以下为药用植物交换网络;所收集的姓名仅限于居住在村庄内的人,作为全网分析方法的边界。除了社会关系数据外,我们还收集了每个举报人的人口统计数据,包括性别、年龄(以年为单位)、亲属关系、在该村居住的年数和在该家庭居住的年数。由于每个村的一些举报人不是村族的成员(例如,教师和他的妻子,来自另一个村的Tsimane,但居住在研究的村庄),他们被视为单独的宗族用于描述分析(宗族5和宗族9),被排除在统计分析之外。
我们还评估了园林管理者的药用植物知识。我们首先让两个村庄的20名男性和女性自由列出他们知道的药用植物,这样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知识调查,包括结构化的问题,根据它们在自由列出的频率和位置或它们的“显著性”来选择16种药用植物(Thompson and Zhang 2006)。随机选取3个最高或最低显著性的物种和4个中等显著性的物种组成3个显著性类群。此外,我们分别分析了女性和男性的免费列表,并选择了另外三种只被女性列出的物种和三种只被男性列出的物种。在知识调查期间(可在http://icta.uab.cat/Etnoecologia/Docs/ [423] -lektests.pdf)时,当地助手会读出所选药用植物的方言名称,询问园丁是否认识这种植物,如果认识,请列出该植物最多三种不同的药用用途。每个已知物种的平均用途被用来评估个体的药用植物知识。
分析
我们使用丰富度作为家庭花园多样性的代表,即,每个信息提供者的花园中不同物种的数量。使用库存数据测量每个信息提供者的家庭花园植物物种丰富度。总丰富度是指每个提供信息的花园所记录的不同物种的数量(包括那些具有药用、食品、手工和其他用途的物种)。药用植物丰富度是指每个供述花园所列的具有药用价值的不同植物种类的数量。
我们记录了受访者给出的方言名称(Hanazaki et al. 2000, Perrault-Archambault and Coomes 2008),然后根据该地区以前的民族植物学研究(见附录1)确定了它们的科学对应名称,并分配了代码来计算丰富度。例如,本地名称seviria而且vira vira”是指单一植物物种的同义词,Cymbopogon citratus,因此,为避免重复计算,两个本地名称都分配了相同的代码。当由于无法获得这方面的信息而无法将方言名称与植物命名法联系起来时,我们为信息提供者提供的所有方言名称分配了唯一的代码。这可能会导致对物种丰富度的高估,因为其中一些方言名称可能指的是同一个物种。此外,这可能导致我们低估了物种的实际数量,因为一个单一的方言名称可能指不同的物种;Cavalcanti和Alburquerque(2013)称之为“隐藏的多样性”。我们按村庄、宗族、园丁的性别和年龄群描述了家庭花园的整体组成。为此,利用亲属关系数据将举报人分配到确定的9个不同宗族中的一个,并将举报人分为4个年龄组(≤25岁、26-35岁、36-45岁和> 45岁)。
社会网络分析
利用社会交换网络上的信息,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网络矩阵,并为每个村庄(群体层面)和每个告密者(个人层面)计算了一组基于图表的度量(McCarty and Molina 2015)。信息被视为无方向性的,并使用Windows的UCINET6-Netdraw进行分析。用多名称生成器方法获得的提名被按村庄聚合在一个文件中,因为我们认为种植材料经常与相关知识一起流动;换句话说,当人们提供或接收种植材料时,他们通常也会提供或接收关于如何种植和使用该物种的解释(Reyes-García et al. 2013)。对于每个村交换网络,我们计算:(1)规模,或网络中的人数;(2)密度,或网络中现有连接的比例相对于最大可能连接数(0-1);(3)中心化,或少数人集中现有联系的倾向(以百分比表示);(4)互惠,或互惠关系的程度。我们为网络中的每个人计算了三种中心性度量(Freeman 1977, 1979, Wasserman和Faust 1994, Everett和Borgatti 2000):程度,或与一个人直接相连的人数;中间性,或一个特定的人(自我)在连接网络中其他人的路径中出现的程度; and egobetweeness, or the number of peopl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only through the ego, a measure that captures the importance of a person in her or his personal network. Data were treated as undirected to capture the existence of a relation regardless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nomination.
我们计算了一个内外指数(E-I指数;Krackhardt and Stern 1988)的研究,探讨了宗族成员、性别和园丁年龄对知识和植物材料交流的影响。E-I指数建议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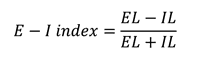 |
(1) |
其中EL为医学知识与植物材料的外部交流次数,EI为医学知识与植物材料的内部交流次数。
因此,假设一个网络被划分为许多相互排斥的群体(这里是宗族、性别或年龄群体),E-I指数评估外部和内部交流之间的关系,即相对同质性,或人们倾向于与与自己相似的人联系,导致群体内的优先交流。E-I指数范围从−1(所有平局都在组内)到+1(所有平局都在组外)。当一个组的内部和外部联系数量相同时,E-I指数= 0。排列测验(N= 5000),以评估网络E-I指数是否与预期显著不同。
统计分析
为了估计被调查者管理的药用植物丰富度与被调查者的中心性度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运行了泊松多元回归,这足以用于计数数据。我们首先测试了程度中心性是否与药用植物丰富度相关,同时控制了研究表明影响家庭花园多样性的其他因素。具体来说,我们回归中的控制包括:村庄或住所、宗族成员、性别、年龄(以年为单位)和年龄平方(Age2;控制年龄与医学知识之间关系的非线性,因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可能会下降)、在村里居住的年数(控制流动性)、在同一房子居住的年数(作为家庭园艺年龄的代理)和个人的药用植物知识。我们使用Mac的STATA 13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提斯曼家花园的丰富性
共清点了111种植物,其中45种被用作药物。两个村庄的园林总丰富度较高且分布均匀,在较偏僻的村庄和较偏僻的村庄分别有86种和83种植物。食物是最常见的用途,其次是医药、手工和其他用途。较不孤立的村庄的居民平均拥有11.58种(SD = 8.53)植物,其中1.90种(SD = 2.27)具有药用价值。在较偏僻的村庄,一名通报者平均维护了13.67种植物(SD = 7.49),其中药用植物3.54种(SD = 2.87)(图2)。
在较不孤立的村庄,妇女维持2.75株(SD = 2.58),男子维持0.96株(SD = 1.39)。一名妇女在自家花园里种了12种药用植物,但17名(30.90%)报案人一株也没有,其中12名为男性。在更偏远的村庄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那里的妇女在家里的花园里也种植了更多的药用植物(4.29;SD = 3.07),男性(2.64;SD = 2.37), 5名举报人没有(16%),其中3名为男性(图2)。
在家庭菜园中最常见的品种是柑橘类植物,如橙子(素类)和葡萄柚(柑橘天堂金花蛇),还有桃棕榈(Bactris gasipaes)、芒果(Magnifera籼)和棉花(Gosipyum取得).棉花几乎全由妇女种植。家庭菜园中最常见的药用植物是姜(生姜)、烟草(Nicotina烟草)和大蒜草(Petiveria alliacea).在药物被报告为使用的总次数中,15%用于治疗普通流感,10%用于治疗一般疼痛,10%用于治疗皮肤真菌感染,5%用于治疗腹泻和胃病、受伤、黄蜂蜇伤和皮肤寄生虫。
医学知识与植物材料交流网络的结构
小隔离村有48名园丁参与到药物植物交换网络中,大隔离村有37名园丁参与(图3)。这些网络具有低密度(0.034 vs. 0.063,小隔离村vs.大隔离村)、低集中度指数(8.08% vs. 6.28%)和低互惠性(0.0317 vs. 0.109)的特征,即网络中的连接相对较低且不互惠。总的来说,这两个网络都显示出了不对称和等级,这意味着有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联系。
我们发现,以氏族成员和性别计算的E-I指数在药用知识和植物材料的交流中存在不同的模式,但不以年龄组计算(图4)。当以氏族成员分组时,较大的氏族(2、3、8)往往在同一氏族内部进行更多的交流,而较小的氏族(1、4、6、7)则主要进行外部交流。排列检验显示,较不孤立的村庄的部落间E-I指数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异(P< 0.05),说明不同氏族的交换模式不同。性群体表现出同质性,大部分交流发生在同性群体内部;这一差异在两个村庄都很显著(P< 0.05)。交换多发生在年龄组之间,各年龄组间E-I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中心的措施
平均而言,更偏远的村庄和女性的中心性指标更高。平均度值是2.96 (SD = 2.90)和4.17 (SD = 2.48)的女性越来越更加孤立的村庄,分别和1.15 (SD = 1.36)和3.35 (SD = 3.12)对于男人来说,分别表明女性交换(或接收)药用植物有更多的人比男性(图3)。中间性的平均价值中心遵循类似的模式,和女人在这两个村庄有一个类似的值(= 80.70,不孤立的村庄SD = 127.56;平均值= 81.59,标准差= 76.50,在较偏僻的村庄),这意味着平均而言,每名女性联系了80对其他情况下不相关的信息提供者。在这个变量中有很大的变化,这表明一些女性在网络中比其他人有更明显的集中作用。男性的平均中介值较低(较偏僻的村庄27.30,SD = 56.99;比较孤立39.84,SD = 184.02)。在中介关系中,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大的差异,这表明男性在桥梁作用上的差异更大,尤其是在更孤立的村庄。同样,女性自我中介变量的平均值也显著高于女性(非孤立村庄5.78,SD = 10.98;较孤立村8.17,SD = 9.59)与男性相比(较孤立村0.82,SD = 1.94;更孤立的6.71,SD = 12.38),尽管男性的自我中介性表现出比女性更大的差异。
药用植物的丰富度与交换网络的中心地位
我们分析了举报人在家庭花园中的药用丰富度与举报人在药用植物交换网络中的位置之间的联系(通过中心性度量进行评估;程度中心性,衡量与一个人有直接联系的人的数量,在统计上与家庭花园的药用丰富度有显著的关系。这种关联对于所有的回归都是稳健的。在所有模型中,变量“男性”显示出与药用植物丰富度更大、更一致的关联,这表明女性在这些网络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在模型A中,我们在控制了村庄、性别和年龄的情况下,检验了一个人的程度中心性与其在家中种植的药用植物物种丰富度之间的相关性(表3)。结果表明,一个人的程度中心性与药用植物物种丰富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系数= 0.122,P< 0.0001)。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交换网络中拥有的联系越多,这个人在她或他的菜园中保持的药用植物的丰富程度就越高。孤立度较低的村庄虚拟变量(coeff。= 0.454,P= 0.004)表示较偏僻村庄的被调查者的药用植物丰富度高于较偏僻村庄的被调查者。结果还表明,女性的家庭药用植物丰富度高于男性(coeff。=−0.621,P< 0.0001),具有较高药用植物知识的人(coeff。= 0.502,P= 0.008)倾向于在自家花园中保持较高的药用物种丰富度。然而,年龄与家庭花园的药用丰富度没有显著相关。
模型B与模型A相似,只是我们用一组虚拟变量来控制宗族成员,而不是村庄。与前一个模型一样,我们发现程度中心性与家庭花园中更大的药用丰富度相关(coeff。= 0.127,P< 0.0001)。宗族2、宗族3、宗族4和宗族8的家庭药用植物丰富度低于宗族6,宗族1和宗族7的家庭药用植物丰富度高于宗族6(见表3)。
在模型C中,我们排除了年龄和年龄²变量(在之前的模型中不显著),并添加了一个人在这个家庭居住的年数。与前两个模型一样,我们发现程度中心性与较高的药用植物丰富度(coeff)相关。= 0.126,P< 0.0001)。在这个模型中,变量“male”(coeff。=−0.641,P< 0.0001)和居住年数(coeff。= 0.032,P= 0.003)与药用植物丰富程度相关,这表明拥有花园时间较长的女性的花园中也有更多的药用植物。
在我们最终的模型D中,我们控制住在村子里很多年。我们再次发现,程度中心性和丰富度之间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正相关(coeff。= 0.136,P< 0.0001)。与之前的模型一样,男性也与丰富度显著相关,正如在村庄居住的时间一样,这意味着在同一村庄居住时间越长的人,其家园的药用植物丰富度越高。
我们通过运行最佳模型的一组变体(表3,模型C;R²= 0.25)。在我们最初的两个鲁棒性测试中(见表4,模型a和b),我们使用中介中心性和自我中心性而不是程度中心性来改变解释变量。在第三个稳健性模型(c)中,我们将结果变量改为总丰富度,并保留与模型c中相同的对照。最后一个稳健性模型(d)通过拟合Tobit多变量回归而不是Poisson多变量回归模型,探讨了在数据中进行审查(18人没有任何药用植物)可能产生的影响。鲁棒性分析结果证实了其他中心性指标也与药用植物丰富度相关。鲁棒性分析还表明,程度中心性与家庭花园的总丰富度(coeff)呈正相关。= 0.092,P< 0.0001)。最后,在运行Tobit多元回归模型(coeff。= 0.457,P< 0.0001)。总之,结果表明,表3中发现的关联对于规范模型中的更改是稳健的。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评估通过社会网络进行药用植物交换对家庭药用植物丰富度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提斯曼的社会组织,特别是亲属关系和性别关系,显著影响交换模式。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在网络中处于更中心位置的人(即拥有更高中心性度量的人)在他们的花园中保持了更大的药用植物丰富度,以及总丰富度。在她们的菜园中,女性的药用植物的丰富程度也高于男性。
先前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塑造了小规模社会的社会交流模式,例如影响作物多样性(Leclerc和Coppens d 'Eeckenbrugge 2012, Labeyrie等人2014)和当地生态知识(Salpeteur等人2015)。研究人员还认为,种植材料交换绝非自由流动(Coomes和Ban 2004),而是通常局限于亲缘关系网络(Aguilar-Støen et al. 2009, Buchmann 2009),在这种网络中,女性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Boster 1985, Sereni Murrieta和Winklerprins 2003)。正如在其他地方所表明的那样(Coomes和Ban 2004),这种模式也可能增加了为家庭花园获取新种植材料的机会。例如,在秘鲁亚马逊的阿丘阿尔人中,种子或插枝等种植材料主要通过母系亲缘网络传播,尤其是从雌性到雌性(Perrault-Archambault和Coomes, 2008年)。对阿丘阿尔人来说,传统上园艺是妇女的责任,就像在其他亚马逊社会一样,花园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高,给它的主人带来威望(Descola 1986,引用在Perrault-Archambault和Coomes 2008)。
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些之前的研究,表明提斯曼人之间的知识和植物材料的交换不是随机的,而是嵌入在基于亲属关系和性别关系的网络中。结果表明,网络具有性别差异,呈现同质性,其中女性表现突出。提斯曼的社会组织可以帮助解释我们的发现。它主要基于亲属关系,在一个村庄内,大家庭的家庭在空间上聚集在一起。提斯曼人的社交活动包括互访,这是保持密切关系的必要手段。访问通常发生在同性亲属和affines之间(Ellis 1996),这将促进同性和氏族成员之间的交流,也解释了为什么较大的亲属群体往往有更多的交流。提斯曼妇女被认为是主要的保健监护人,负责满足其家庭的初级保健需要(Chiccón 1992)。园艺似乎也主要是女性的领域,这是一种与她们在家庭领域中照顾者的职责相关的生产性角色。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女性都是杰出的花园管理者(见Howard 2006年的评论),这也与传统社区社会关系的维护、社区粮食安全和健康有关(Finerman和Sackett 2003年,Lope-Alzina和Howard 2012年)。家务为妇女提供了从事自给生产的机会,而这种生产不违反关于男性在生产领域(例如,作为主要提供者)或关于妇女家务的性别规范,为妇女提供了权威、自主和地位的来源,并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发展专业知识并根据其文化角色提供可见的认可手段的场所(Howard 2006年,Lope-Alzina和Howard 2012年)。 Homegardens are also considered as arenas for sociality and experimentation and are a source of pride and self-esteem for women (Heckler 2004). The Tsimane’ do not seem to deviate from this pattern.
社交网络中的位置为通过网络中的其他人访问资源和知识提供了可能性和约束(Calvet-Mir et al. 2012, Kawa et al. 2013),因为在每个特定的情况下,网络可以支持或限制对这些人的访问。获得他人的种植材料对于发展和保持家庭花园的多样性很重要(库姆斯2010年)。在本研究中,网络中心性似乎与一个人在药用植物交换网络中的表现有关,因为在网络中中心性较高的人,其家园的药用植物丰富度也较高。与男性相比,女性在交换网络中更处于中心地位,这一发现与女性作为主要花园管理者的突出角色非常吻合。女性具有较高中心性指标的性别网络可能表明她们有更多机会获得药用种植材料和相关知识。其他因素,如花园的主人照料花园的年数和一个人在同一村庄居住的年数,也解释了提斯曼家花园里药用植物的丰富程度。
我们承认我们的解释可能存在缺陷;我们的数据只捕获了单个时间点上网络结构的快照,而这是有效的,假设网络结构是稳定的(Howison et al. 2011)。数据也很有限,因为它们只收集发生在同一村庄内的交易;与“居住在其他村庄的提斯曼人”的交流不被考虑,与非提斯曼人(即与商人和研究人员)的交流也不被考虑。这限制了我们研究结果的广度和解释力,因为社交网络是动态的,并且嵌入在更高的局部和区域尺度的网络中。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分析是追踪提斯曼族家庭药用种植材料和知识不均匀流动的一个合适和有用的工具。家庭药用植物丰富度和植物总物种丰富度与园丁在交换网络中的中心性相关,中心性越高的人保持的物种丰富度越高。因为女性通常拥有更高的中心地位,她们也比男性保持更大的物种丰富度。同样,花园被照料的年数和一个人在同一村庄居住的年数与更大的药用植物和植物总物种丰富度呈正相关。此外,围绕亲属和性别的社会组织显著影响药用植物知识和种植材料交换模式,突出表明与农业生态条件、园丁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特定文化的社会结构一起是家庭花园植物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决定因素。这表明农业多样性和文化密切相关(Howard 2006, Leclerc and Coppens d 'Eeckenbrugge 2012)。
了解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热带家庭菜园的物种多样性,特别是药用植物多样性,可以帮助决策者、卫生服务提供者和当地社区更好地了解如何在当地促进和保护药用植物,以便继续为缺乏生物医学卫生保健系统的人提供当地可获得的、文化上合适的、经济上可负担的卫生保健选择。这种理解促进使用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生物文化方法,提供文化上适当的手段,以减少全球和当地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损失。
致谢
本研究由欧洲研究理事会根据欧盟第七框架计划(FP7/2007-2013)/ERC资助协议FP7-261971-LEK资助Reyes-García。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举报人,感谢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时间和知识,并友好地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家园。我们也感谢提斯曼大议会和CBIDSI为圣博尔哈提供的后勤支持和办公设施;我们感谢Marta Pache、Paulino Pache、Vicente Cuata、Sascha Huditz和Giuliana Castañeda提供的现场援助,以及Maximilien Guèze提供的制图帮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深思熟虑的建议。
文献引用
Aceituno-Mata l . 2010。工作室etnobotánico y agroecológico de la Sierra Norte de Madrid。论文。马德里大学Autónoma,马德里,西班牙。(在线)网址:http://bibdigital.rjb.csic.es/PDF/Aceituno_Estud_Etnobot_Sierra_N_Madrid_2010.pdf.
Aguilar-Støen, M., S. R. Moe, S. L. Camargo-Ricalde。2009.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Candelaria Loxicha,家庭花园维持了作物多样性,并提高了农场的适应能力。人类生态学37(1): 55 - 77。http://dx.doi.org/10.1007/s10745-008-9197-y
Ban, N.和O. T. Coomes. 2004。秘鲁亚马逊地区的家庭花园:种植材料的多样性和交换。地理复习94(3): 348 - 367。http://dx.doi.org/10.1111/j.1931-0846.2004.tb00177.x
Bernholt, H., K. Kehlenbeck, J. Gebauer和A. Buerkert. 2009。尼日尔尼亚美城市和城郊花园的植物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农林复合经营系统77(3): 159 - 179。http://dx.doi.org/10.1007/s10457-009-9236-8
波斯特,1985。给无所不知的告密者的安魂曲:这个老女孩还有生命。177 - 198页在j·w·d·多尔蒂,编辑。认知人类学方向。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美国伊利诺斯州香槟市。
曼(c . 2009。古巴家庭花园及其在社会生态恢复中的作用。人类生态学37(8): 705 - 721。http://dx.doi.org/10.1007/s10745-009-9283-9
卡尔维特-米尔,L., M.卡尔维特-米尔,J. L.莫利纳,V. Reyes-García。2012.种子交换是一种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个案研究在Vall Fosca,加泰罗尼亚比利牛斯,伊比利亚半岛。生态和社会17(1): 29。http://dx.doi.org/10.5751/es-04682-170129
卡瓦尔康蒂,博士,阿尔伯克基大学。2013。巴西东北部药用植物的“隐藏多样性”:诊断与保护及生物勘探前景。循证补充和替代医学2013: 102714。http://dx.doi.org/10.1155/2013/102714
Chicchon, a . 1992。玻利维亚贝尼生物圈保护区Chimane资源的利用和市场参与。论文。佛罗里达大学,盖恩斯维尔,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线)网址:http://ufdc.ufl.edu/AA00003266/00001.
库姆斯,2010年。关于木桩、茎和插枝:传统亚马逊社会中当地种子系统的重要性。专业地理学家62(3): 323 - 334。http://dx.doi.org/10.1080/00330124.2010.483628
Coomes, o.t, N. Ban, 2004。秘鲁东北部一个亚马逊村庄家庭花园的栽培植物物种多样性。经济植物学58(3): 420 - 434。http://dx.doi.org/10.1663/0013 - 0001 (2004) 058 (0420: CPSDIH) 2.0.CO; 2
Daillant, i . 2003。Sens dessus desous:社会和空间组织。生物americain 6。Société d 'ethnologie,南泰尔,法国。
埃利斯,r . 1996。爱好运动:探索玻利维亚低地提斯曼人的社会伦理。论文。圣安德鲁斯大学,圣安德鲁斯,英国。(在线)网址:http://hdl.handle.net/10023/2901.
埃弗雷特,M. P.博加蒂,2005。自我网络中间状态。社交网络27(1): 31-38。http://dx.doi.org/10.1016/j.socnet.2004.11.007
费尔曼,R.和R.萨克特,2003。利用家庭花园来解读安第斯山脉的健康和治疗。医学人类学的季度17(4): 459 - 482。http://dx.doi.org/10.1525/maq.2003.17.4.459
弗里曼,l.c. 1977。一组基于中间性的中心性度量。人与人之间(1): 40 35-41。http://dx.doi.org/10.2307/3033543
弗里曼,l.c. 1979。社交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概念澄清。社交网络1(3): 215 - 239。http://dx.doi.org/10.1016/0378 - 8733 (78) 90021 - 7
Hanazaki, N. J. Y. Tamashiro, H. F. Leitão-Filho和A. Begossi. 2000。巴西大西洋森林海岸的两个Caiçara群落的植物使用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保护9(5): 597 - 615。http://dx.doi.org/10.1023/A:1008920301824
Heckler, S. L. 2004。培养社会性:Piaroa家庭花园组成和功能中的美学因素。人种生物学杂志》上24(2): 203 - 232。
亨利克,J.和J.布罗施,2011。文化传播网络的本质:来自斐济村庄的适应性学习偏差的证据。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B366(1577): 1139 - 1148。http://dx.doi.org/10.1098/rstb.2010.0323
霍普金斯,a . 2011。使用网络中心性措施来解释墨西哥塔比的尤卡特克玛雅人的草药文化能力的个体水平。场的方法23(3): 307 - 328。http://dx.doi.org/10.1177/1525822x11399400
霍华德,2006年。拉丁美洲瑞典菜园和家庭菜园的性别和社会动态。159 - 182页在库马尔和奈尔,编辑。热带家庭菜园:可持续农业林业久经考验的例子。施普林格,Dordrecht,荷兰。http://dx.doi.org/10.1007/978-1-4020-4948-4_10
霍华德,P. L.和G. Nabanoga. 2007。植物有习惯权利吗?对巴干达人(乌干达)进行调查,特别注意性别问题。世界发展35(9): 1542 - 1563。http://dx.doi.org/10.1016/j.worlddev.2006.05.021
豪森,J.威金斯,K.克劳斯顿,2011。利用数字追踪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有效性问题。信息系统协会杂志12(12): 767 - 797。
怀H.和A.汉密尔顿。2009。传统家居花园的特点与功能综述。中国生物学前沿4(2): 151 - 157。http://dx.doi.org/10.1007/s11515-008-0103-1
卡瓦,N. C.麦卡蒂,C. R.克莱门特,2013。亚马逊农村木薯品种多样性、社会网络和分布限制。当代人类学54(6): 764 - 770。http://dx.doi.org/10.1086/673528
凯伦贝克和B. L.马斯,2004。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家庭菜园的作物多样性和分类。农林复合经营系统63(1): 53 - 62。http://dx.doi.org/10.1023/b:agfo.0000049433.95038.25
克莱克哈特和斯特恩,1988。非正式网络与组织危机:一个实验模拟。社会心理学季刊51(2): 123 - 140。http://dx.doi.org/10.2307/2786835
库贾维斯卡先生,帕尔多·桑塔亚纳先生。2015.欧洲移民在南美洲对药用植物的管理。民族药物学杂志172:347 - 355。http://dx.doi.org/10.1016/j.jep.2015.06.037
库马尔,B. M.和P. K. R.奈尔,编辑。2006.热带家庭菜园:可持续农业林业久经考验的例子。施普林格,Dordrecht,荷兰。http://dx.doi.org/10.1007/978-1-4020-4948-4
Labeyrie V., B. Rono和C. Leclerc. 2014。社会组织如何塑造作物多样性:肯尼亚山塔拉卡农民的生态人类学方法。农业与人类价值31(1): 97 - 107。http://dx.doi.org/10.1007/s10460-013-9451-9
勒克莱尔,C.和G.科本斯·德·埃肯布鲁日。2012.作物遗传多样性的社会组织。G × E × S相互作用模型。多样性4(1):学会年会。http://dx.doi.org/10.3390/d4010001
莱赫,北卡罗来纳州,1999年。秘鲁亚马逊东北部帕卡亚-萨米拉国家保护区的家庭花园、栽培植物多样性和种植材料交换。论文。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
Lope-Alzina, d.g. 2014。玛雅-尤卡塔卡地区的食物供应的红色社区:玛雅-尤卡塔卡地区的食物供应的主要保障。盖亚Scientia卷特Populações Tradicionais:199-215。(在线)网址:http://periodicos.ufpb.br/ojs/index.php/gaia/article/view/22430/12539.
洛佩-阿尔吉娜,D. G.和P. L.霍华德,2012。家居花园的结构、组成和功能:以Yucatán半岛为重点。Etnoecologica9(1): 17-41。
C.麦卡蒂和J. L.莫利纳。2015。社会网络分析。631 - 657页在h·r·伯纳德和c·g·格雷夫利,编辑。文化人类学方法手册。第二版。Rowman和Littlefield, Lanham, Maryland, USA。
佩诺特-阿坎博,M.和O. T.库姆斯,2008。秘鲁亚马逊科连特斯河沿岸家庭花园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分布。经济植物学62(2): 109 - 126。http://dx.doi.org/10.1007/s12231-008-9010-2
Piland, r . 2000。玻利维亚提斯曼尼农业relación con la conservación en la Reserva de la Biosfera Estación Biológica del Beni。329 - 344页在玻利维亚生物多样性中心,conservación y manejo en la región de la Reserva de la bioosfera Estación Biológica del Beni。SI /马伯系列4。史密森学会,华盛顿特区,美国
饶M. R.和R. B. Rajeswara Rao。2006。热带家庭花园里的药用植物。205 - 232页在库马尔和奈尔,编辑。热带家庭菜园:可持续农业林业久经考验的例子。施普林格,Dordrecht,荷兰。http://dx.doi.org/10.1007/978-1-4020-4948-4_12
Reyes-García, V., R. Godoy, V. Vadez, L. Apaza, E. Byron, T. Huanca, W. R. Leonard, E. Pérez,和D. Wilkie. 2003。玻利维亚提斯曼的美洲印第安人广泛分享民族植物学知识。科学299(5613): 1707。http://dx.doi.org/10.1126/science.1080274
Reyes-García, V. J. L. Molina, L. Calvet-Mir, L. Aceituno-Mata, J. J. lasstra, R. Ontillera, M. Parada, M. Pardo-de-Santayana, M. Rigat, J. Vallès, T. Garnatje. 2013。伊比利亚半岛家庭园丁的种质交换网络和农业生态知识。民族生物学与民族医学杂志9(1): 53 - 62。http://dx.doi.org/10.1186/1746-4269-9-53
Reyes-García, V., V.瓦兹,T.万卡,W.伦纳德,和D.威尔基。2005。野生植物的知识和消费:玻利维亚亚马逊两个提斯曼人村庄的比较研究。民族植物学研究与应用“,3:20 1 - 207。(在线)网址:http://journals.sfu.ca/era/index.php/era/article/view/71/58.
Reyes-García, V. S. Vila, L. Aceituno-Mata, L. Calvet-Mir, T. Garnatje, A. Jesch, J. J. lasstra, M. Parada, M. Rigat, J. Vallès,和M. Pardo-de-Santayana。2010.性别化的家庭花园:伊比利亚半岛三个山区的研究。经济植物学64(3): 235 - 247。http://dx.doi.org/10.1007/s12231-010-9124-1
Salpeteur, H. Patel, A. L. Balbo, X. Rubio-Campillo, M. Madella, P. ajjithprasad, V. Reyes-García。2015.当知识跟随血缘:亲属群体和传统生态知识在古吉拉特邦(印度)半游牧牧民社区中的分布。当代人类学56(3): 471 - 483。http://dx.doi.org/10.1086/681006
Sereni Murrieta, R. S.和A. m.g. A. Winklerprins. 2003。水之花:巴西亚马逊河下游一个caboclo社区的家庭花园和性别角色。文化和农业25(1):形成反差。http://dx.doi.org/10.1525/cag.2003.25.1.35
汤姆斯,E.和P.云顿,2010。家庭花园和瑞典的植物使用和管理:来自玻利维亚亚马逊的证据。农林复合经营系统80(1): 131 - 152。http://dx.doi.org/10.1007/s10457-010-9315-x
Thompson, E. C.和J. Zhang, 2006。比较文化显著性:使用自由列表数据测量。场的方法18(4): 398 - 412。http://dx.doi.org/10.1177/1525822x06293128
沃克斯,R. A. 2004。干扰药典:来自潮湿热带的医学和神话。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94(4): 868 - 888。http://dx.doi.org/10.1111/j.1467-8306.2004.00439.x
沃瑟曼,S.和K.浮士德,1994。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应用剑桥大学出版社,英国剑桥。http://dx.doi.org/10.1017/cbo9780511815478
魏泽尔,A.和S.本德,2003。古巴家庭菜园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其对家庭粮食供应的意义。农林复合经营系统(1): 57 39-49。http://dx.doi.org/10.1023/A:1022973912195
Wezel, A.和J. Ohl, 2005。远离城市中心是否影响家庭花园和农田的植物多样性?:一个来自秘鲁亚马逊雨林Matsiguenka的案例研究。农林复合经营系统65(3): 241 - 251。http://dx.doi.org/10.1007/s10457-005-3649-9
杨亮、S. Ahmed、J. R. Stepp、米昆、赵莹、马俊杰、梁超、裴硕、怀华、徐国刚、a.c. Hamilton、郑伟。杨,薛东。2014。滇西北纳西医农家庭药用民族植物学比较研究。民族生物学与民族医学杂志10: 6。http://dx.doi.org/10.1186/1746-4269-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