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2012作者。由韧性联盟授权在此发布。
去pdf本文的版本
去pdf本文的版本
以下是引用这篇文章的既定格式:
沈晓霞,吕志忠,李舒,陈宁。2012。西藏圣地:了解传统管理制度及其在现代保护中的作用。生态和社会 17(2): 13。
http://dx.doi.org/10.5751/ES-04785-170213
研究
沈晓霞,吕志忠,李舒,陈宁。2012。西藏圣地:了解传统管理制度及其在现代保护中的作用。生态和社会 17(2): 13。
http://dx.doi.org/10.5751/ES-04785-170213
西藏圣地:理解传统管理体制及其在现代保护中的作用
1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自然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1008712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自然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1008713.北京山水保护中心,北京100871
摘要
圣地建立在重视土地和生命的土著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基础上,被认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大贡献。然而,人们对这些传统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例如,圣地的分布和规模,它们的管理和现状)缺乏了解,特别是对藏区内的那些圣地。2004年至2007年,我们对中国西部藏区主要形式之一的神山进行了调查,对其传统管理体制进行了记录。我们在一个GIS中绘制了154座圣山,估计它们的平均大小为25.9公里2(范围0.6 - -208.4公里2),有更大的宗教意义的圣山覆盖范围更广。寺院在保护圣山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3.1%的人指定专人管理圣山,63.9%的人巡视圣山。官方自然保护区与神山有明显的空间重叠,但很少有保护区与当地社区或寺院建立了土地资源管理合作关系。我们认为,西藏神山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不仅因为其覆盖面积相当大,而且因为当地对神山保护的参与度很高。我们认为西藏圣地是一个景观级的保护属性。在西部地区推进西藏圣地保护,需要将西藏的圣地纳入正式的保护网络,赋予当地社区参与保护和管理的权利。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参与式测绘,保护区,藏区圣地,传统土地管理
介绍
具有特殊社会精神背景的土著人民所认为的圣地,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群体中都有发现(Bhagwat和Rutte 2006, Dudley et al. 2006)。它们以各种形式和不同的空间尺度出现,例如单一植物物种(Colding和Folke 2001, Kufer等人2006),墓地(Mgumia和Oba 2003, Wadley和Colfer 2004),神圣的树林(Gadgil和Vartak 1974, Malhotra 2001),甚至用于宗教崇拜的整座山或湖泊(Maharana等人2000,Castro和Aldunate 2003, Jain等人2004,Xu等人2005)。神圣的地点世世代代都受到当地人的精神价值的保护,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保护区形式(Dudley et al. 2009)。研究表明,圣地崇拜的传统做法可能对保护濒危物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重大贡献(Decher 1997, Mgumia和Oba 2003, Bhagwat et al. 2005a, 2005b, Bossart et al. 2006),而很少有研究记录了这些传统做法背后的社会机制(Malhotra 2001, Tengö et al. 2007)。许多学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提倡承认当代保护系统中圣地的价值,并在过去二十年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Daniels et al. 1993, Xu et al. 2005, Bhagwat and Rutte 2006, Dudley et al. 2006, 2009)。在中国西部,作为藏传佛教实践的一部分,受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前身)的影响,西藏的圣地已经被崇拜和保护了几个世纪(Feng 2005, Salick et al. 2007)。西藏圣地是神灵、自然神灵和精神领袖的住所,或与之相关(Jamtso 2005)。它们有几种主要的形式,包括圣山、湖泊、遗迹、禁区(国际扶轮Vgag藏语)和朝圣路线(Ma 2005)。它们基于佛教的观点,重视土地和所有生物(Nan 2001a)。保护山川湖泊的神灵,尊重一切形式的生命,被认为有利于当地人、他们的农田和牲畜的福祉(He 2005),并为追求永恒幸福的个人积累功德(Jamtso 2005)。
中国西部建立了大量自然保护区(中国官方保护区的主要形式),占中国所有自然保护区面积的75%以上(中国环境保护部(MEPC) 2008)。然而,由于人员、能力和资金支持不足,储备管理往往是无效的(Liu et al. 2003, Xie 2004)。同时,中国西部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它包含40多个民族,占中国全部民族人口的89% (Li et al. 2008)。研究表明,这些民族中有很高比例的文化实践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相一致(Xu et al. 2005)。为了提高自然保护区的有效性,提出了一种融合文化保护的保护政策(Luo et al. 2001, Xu et al. 2005, Xu and Melick 2007),但尚未得到区域政府的采纳。因此,确定植根于土著文化和传统做法的有效保护方法非常重要。
中国藏区圣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学视角,最近转向保护视角(Luo et al. 2001, Nan 2001b, Ma 2005, Li et al. 2008)。西藏圣地在保护中的意义集中在它们的广泛分布(Xu et al. 2005, Shen et al. 2007)以及它们在保护成熟森林(Zou et al. 2005, Salick et al. 2007, Xiang et al. 2008)和濒危物种(Anderson et al. 2005)方面的功能。然而,我们对西藏圣地的空间分布和管理知识还很薄弱。以往的研究多为文化实践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概念性讨论(Li et al. 2008)。实地研究的重点是测量西藏圣地内的生物多样性(Anderson等,2005,Zou等,2005,Salick等,2007,Xiang等,2008),而不是管理结构。
本文首次系统地研究了西藏圣地的大尺度空间分布、管理制度及其潜在保护作用。我们以藏区圣地的主要形式之一神山为重点,进行了大尺度测绘。目的:(1)了解西藏圣地的空间格局;(2)估算西藏神山的数量和面积;(三)记录西藏圣地的管理办法;(4)比较圣地与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布局与管理体系,探讨二者如何相互整合,相互支撑。
方法
研究区域
我们在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北纬27º58′-34º20′,东经97º22′-102º29′,图1)进行了研究。它由18个县组成,土地面积153002公里2(甘孜州志委员会,1997)。藏族人口占甘孜总人口的76%;其他民族(如汉族、羌族和彝族)主要生活在州边界(CGPA 1997)。甘孜位于横断山脉,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温带生态系统之一(Mittermeier et al. 2004)。该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平均海拔约3500米(1321 - 7556米)(CGPA 1997)。我们主要研究的海拔2,500米以上的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林(Bethula utilis,b . platyphylla,杨树davidiana)、常绿阔叶林(Quercussp.和松萝对)、落叶针叶林(落叶松属potaniniivar。macrocarpa,l . potaninii)、常绿针叶林(松果体,云杉,冷杉属,Cupressus属),亚高山灌木(杜鹃而且萨比娜spp.)和高寒草甸(Zhang 1997)。
我们在甘孜县的6个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县城的海拔范围很广:丹巴(1850米)、雅江(2580米)、襄城(2860米)、道府(2980米)、德格(3270米)、理塘(4010米)(图1)。这六个县占甘孜地区的33%。
实地调查与数据分析
几乎所有的西藏圣地都有他们相关的寺院(次仁济美和扎西多杰,个人交流)。由于修道院保存着有关其相关圣地的关键信息(Nan 2001b),我们访问了修道院来收集有关圣地的信息。我们采访了每个修道院的当地宗教领袖、社区领袖和知识渊博的村民。我们使用了一种参与式的制图方法(Chambers 1994)来定位修道院、圣山及其边界。这些信息记录在1:10万的地形图上,然后用全球定位系统(GPS)进行验证。我们还记录了神山的管理结构、每座山的意义、禁忌、传说和历史事件等信息。为了展示各种形式的圣地的空间分布及其与神山的关系,我们选取了德格县的宗萨尔寺,并绘制了寺院周边的所有圣地及其附属村庄的地图。根据神山影响的空间范围,我们将神山划分为三个层次(Ma 2005):(1)村庄层面——由一个或几个邻近的村庄所崇拜;(二)县一级,由一个县或者相邻的县设立;(3)整个康区或整个藏区所崇拜的康区或藏级(康区位于藏区东部,以方言为标准是整个藏区的三个区之一)。此外,还有单身家庭崇拜的神山;但这些区域通常很小,在这项研究中没有记录。我们使用ArcGIS 9.2 (ESRI, California, USA)对地理信息系统(GIS)中的地理空间数据进行数字化和分析。利用GIS计算了各个神山的土地面积。我们将土地面积对数转换为正态性,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Fisher最小显著性差异(LSD)检验,在SPSS 15.0 (SPSS Inc., Illinois, USA)中比较不同层次的神山土地面积。我们估计了总数(N)甘孜境内的圣山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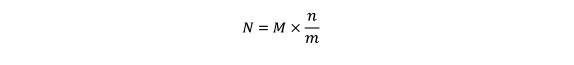 |
(1) |
在哪里米为甘孜境内寺院总数(米= 515,戴2007),n是采样神山的数量,和米为抽样寺院数量;
神山的总面积(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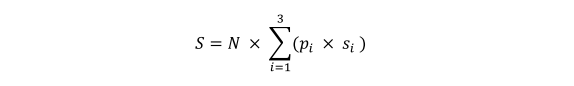 |
(2) |
在哪里我是等级森严的神山,p神山在各个等级中的百分比,和年代为神山各等级平均土地面积。
我们从四川省林业厅收集了6个调查县保护区边界的GIS数据。我们使用ArcGIS 9.2中的空间分析工具来研究我们绘制的圣山与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空间关系。
结果
西藏圣地的空间格局与禁忌
我们以宗萨尔修道院的圣地及其附属村庄为例,说明圣地在传统藏族社区中的分布情况(图2a)。五种形式的圣地被确定:圣山、圣湖、禁区、圣物和朝圣路线。神山被认为是山神的住所。它们个头很大,可以从山顶的经幡上辨认出来。它们的空间范围得到了当地修道院和社区的认可。圣湖被认为是河岸神的住所。圣湖的范围被它的自然边缘清楚地界定出来。被禁止的领域(国际扶轮Vgag(藏语)通过当地社区的协议建立,以防止这些地区受到人类的干扰,主要是为了保护关键的神圣区域。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神山神湖重叠。神圣的遗迹与神、自然的灵魂和精神领袖有关,被认为包含神圣和力量,如山神的脚印,著名的“仁波切”(西藏喇嘛和其他高级或受尊敬的老师)使用的洞穴,神占用的泉水。圣物以各种形式出现(如洞穴、石头、悬崖、泉水、树木和小树林),规模小,可以在圣山内外的任何地方。在修道院和圣山圣湖周围发现了朝圣路线,用来朝拜神灵。在修道院周围有三种朝圣路线:靠近修道院的短途路线;穿过该地区重要圣地的中间路线;还有一条很长的线路连接了一个更大区域内的多个修道院和圣地。在所有这些形式的圣地中,圣山的土地覆盖面积最大。神山是亲属身份的重要参照地,因为一个家庭世世代代都会膜拜同一座神山,而且人们相信家族和山神之间存在着精神联系。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圣山,有时几个村庄共享同一座山。寺院位于传统藏族社区的中心(通常包括多个相邻的村庄,在现代之前属于同一个部落)。寺庙附近的圣山受到整个社区或更广泛群体的尊重,这取决于这座山的宗教影响力(图2b)。每逢藏历新年,村民们都要祭拜所属的神山,每年夏天,村民们都要祭拜全社区的神山。
我们发现藏区圣地及其周边社区有一个共同的空间格局,可分为三个区域(图2c):(1)禁区这些地区的行为规定最为严格,例如禁止捕杀动物和收割植物。这个地区只允许举行宗教仪式和朝圣活动;(2)受保护的区域,禁区外的其他神圣区域,禁止狩猎、伐木和农业,但允许放牧(有时是季节性的)和收获非木材林产品。 同样,禁止在圣湖游泳、钓鱼和洗澡;和(3)影响区,整个社区区域包括圣地。在这个领域内,对资源的使用没有严格的禁忌,只要人们遵守不杀生,这是佛教行为的基本原则,包括不杀人。
西藏神山的分布与管理
从2004年到2007年,我们共走访了6个县的74所寺院(每个县12-13所),占全县寺院总数的38.3%。我们记录了213座神山,其中154座被绘制在GIS中。
圣山的数量和大小
我们记录了每个修道院周围2.9座神山的平均值(SD = 2.6,范围0-28)。神山总面积为3990.7公里2,平均个体大小为25.9公里2(n= 154, SD = 38.4 km2射程0.6-208.4公里2)(图3)
我们发现,在更高的等级等级中,神山更少(汗/藏级别有44座;县级78人;91在村庄层面)。三层神山的土地面积不同(F 2117年= 12.980,p< 0.001)。县一级神山(42.2±35.5公里)2)或康/藏水平(53.9±66.3公里)2)显著大于村(17.4±21.7 km)2;迷幻药,p< 0.001;根据我们的调查样本,我们估计甘孜有1480座神山,占地4.6万公里2占甘孜土地总面积的30.1%。
神山管理
神山的管理与它的等级有关(表1)。寺院和当地村庄都参与了神山的管理。寺院在地方法规的制定和维护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保护神山,73.1%的寺院(n= 67)指定特定的监护人,他们通常是修道院的纪律人员,来管理圣山;63.9%修道院(n= 72)在山上有组织的巡逻,但巡逻的范围和频率差别很大。我们把巡逻活动分为不定期和定期两类。不定期巡逻(47.2%)涉及组织不严密的活动。僧侣们在业余时间自愿巡逻,检查动物陷阱和伐木。当地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违规者或有违规者的迹象时,都会向寺院报告,并组织搜查。常规巡逻(16.7%)是指定僧人或村民等特定人员对神山进行巡逻,并固定人数、频率和路线。11个定期巡逻的寺院向巡逻人员提供报酬(物质或金钱)。另有29.2%的寺庙不进行巡逻,但报告称,当人们在朝圣期间游览圣山时,它们发挥了巡逻功能,帮助发现陷阱和抓获偷猎者。
修道院(n= 60)报告神山管理的主要困难是:(1)资金不足(38.3%);(2)资源压力高(30.0%);(3)缺乏法律认可和政府支持(23.3%);(4)人力资源不足(11.7%)。
对圣山的威胁来自社区内部和外部的力量。一般来说,拥有强大传统和组织的社区会经历来自社区外部的神山压力,而没有强大传统的社区则会经历更多的内部压力。48个寺院(70%)报告违规者主要为外来者,其中26.1%为非藏人,如商人和游客。当地社区经常在他们的神山上阻止违纪行为,主要是砍伐和狩猎(图4)。当违纪行为发生,违纪者被村民抓获时,违纪者通常会受到口头警告、没收工具、罚款或送往寺院或当地政府的惩罚。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三起案例记录了村民和外来罪犯在冲突中受伤或死亡的情况。
除了个别侵犯行为外,近年来政府机构和(或)商业公司的剥削活动也有所增加。道路建设(29.7%)、旅游业(29.7%)、采矿(9.5%)和水电开发(1.4%)是寺庙报告的对圣山的新威胁。
神山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
我们发现神山和自然保护区之间有显著的空间重叠。我们调查的6个县有17个自然保护区。我们发现每个都包含至少一座(最多13座)圣山。在绘制的154座神山中,19.3%完全位于保护区内(615.1公里)2在陆地面积上,12.7%与保护区部分重叠(1585.0 km)2), 68.0%位于保护区(1,790.6公里)以外2).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提供了神山与宗萨尔寺周围四个自然保护区的空间重叠(图2a);圣山扩大了受保护地区的范围,并有可能成为多个保护区之间的野生动物走廊。然而,我们记录到,除了一个案例外,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寺庙之间在土地管理方面很少有合作。寺院与负责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县林业部门的合作程度略高(表2)。当地林业部门为2个寺院提供了森林防火资金,并参与或资助了另外5个寺院组织的巡逻活动。1996年,一家寺院通过书面协议获得了当地林业部门的授权,可以管理神山。根据这项协议,他们可以合法地阻止违反他们圣山规定的外人。
讨论
西藏圣地作为景观级保护措施
世界上大多数圣地都很小。在坦桑尼亚,八个被调查的神圣树林的面积从0.1-0.3公顷不等(Mgumia和Oba 2003年)。在印度南部,圣林的平均面积为13.2公顷(n= 25,范围0.2-48.1公顷)(Bhagwat et al. 2005b),而整个印度神圣树林的平均大小估计为9.6公顷(n= 4415,总面积= 42,278公顷)(Malhotra 2001年)。这些神圣的小树林可以有效地保护濒危物种(Jamir and Pandey 2003, Ramanujam and Cyril 2003),但无法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相比之下,我们所绘制的西藏圣山面积非常大,分布非常广泛,可以保护更高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提供清洁水等生态系统服务。我们估算的甘孜神山土地覆盖面积(30.1%)接近当地西藏文化专家的独立估计(30-40%;次仁济美,个人沟通)。神山与其他类型的圣地构成了藏区大规模的圣地景观。
我们发现西藏神山的大小变化很大(范围0.6 - 208.4 km)2,平均= 25.9公里2).虽然神山的覆盖率相当大,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神山的覆盖面积很小(56.8% < 20 km)2).这些圣山可能太小,无法维持大型动物的存活数量。例如,亚洲黑熊,熊属主干一般来说,每辆车的飞行距离为16-202公里2(Reid et al. 1991, Hwang 2003);一些大型猫科动物(如豹)豹属pardus和雪豹Uncia Uncia)需要更大的狩猎面积(Norton and Lawson 1985)。小的圣山不能完全容纳这些物种的种群,但它们可以作为分散个体的大景观之间的“垫脚石”,有助于保护它们(Tischendorf和Fahrig 2000)。等级越高的神山规模越大,因此在区域保护规划中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藏族圣地,作为社区保护区的一种形式;Oviedo 2006, Smyth 2006),已得到当地人民的有效保护,并具有保护濒危物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Anderson et al. 2005, Zou et al. 2005, Salick et al. 2007, Xiang et al. 2008)。在进入和利用方面,西藏圣地可与IUCN的几个保护区类别(IUCN 1994)相媲美:禁区和严格禁止的圣湖类似于第一类(严格自然保护区和荒野区);根据传统法规执行的严格程度,神山可划分为第二类(国家公园)、第五类(保护景观)或第六类(管理资源保护区);寺庙和圣物符合第三类(自然纪念物)定义。在中国西部,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还没有建立在区域生物多样性无偏采样的基础上(Liu et al. 2003)。当地方政府(通常是县级)提出新的自然保护区时,没有考虑到新保护区对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的贡献有多大。将西藏圣地纳入自然保护区网络,可以扩大保护区的覆盖范围和生态系统种类,提高保护区的综合性和代表性。
我们估计西藏神山的总面积大约等于甘孜自然保护区的面积(MEPC 2008)。基于神山与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布局,西藏神山对自然保护区网络的贡献表现为三种形式:(1)保护区内神山为物种的长期存在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维持提供了更大的保障;②与保护区相邻的神山提高了保护区的有效规模,改善了栖息地的连通性;(3)与现有自然保护区不重叠的神山通过当地社区的实践,对保护区体系进行了补充。
尽管西藏圣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在以往的区域保护规划中并未考虑到这一点(Li et al. 2008)。我们不知道这些自然保护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生物多样性的全部种类,也不知道承认西藏神山后,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增加多少。我们建议对西藏地区进行系统的保护规划(Margules and Pressey 2000),包括自然保护区和西藏神山。
整合西藏圣地实践,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效益
西藏圣地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植根于传统的世界观和文化价值观,并通过当地的制度制定(Berkes et al. 2000)。人们相信,保护圣山的完整将取悦山神,并有利于相关社区的福祉。这种信念是自律保护体系的精神动力。当地社区已经制定了保护圣山的规定,以及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应采取何种惩罚措施。最严厉的惩罚是切断寺院和违规者之间的联系。社区内法规的有效性通常取决于寺院或特定喇嘛的崇敬程度、村民对佛教的信奉程度以及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Harris 1991)。我们发现,大多数修道院都在努力防止违规行为,尤其是来自社区外的违规行为。与世界上其他神圣实体一样,西藏当地社区对圣地的保护是自愿的,直接成本很小(North 1990, Bhagwat和Rutte 2006)。虽然有11个受访寺院为巡逻提供了报酬,但每年的报酬很低(每人高达1500元人民币/ 230美元),大约相当于一个储备人员一个月的工资。巡逻活动的范围取决于修道院的能力和决心,差别很大。我们发现,由于资金和人力的限制,只有一小部分寺院组织了定期巡逻。若能得到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在财政和技术上的协助,可大大提高寺院的保护成效。
更好的巡逻活动可以带来更好的保护结果,但反过来可能就不成立了。巡逻活动通常是对外界对圣山及其野生动物的威胁的反应。我们还发现,在没有定期巡逻的情况下,一些传统社区的圣山管理得很好。社区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抵御外部威胁的角色,可以有效防止违规行为的发生。因此,神山的管理效能并不是简单地与寺院的巡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村民的日常活动增加自愿保护工作,也可以加强对神山的保护。
西藏地区大多数自然保护区由于人员和资金支持不足,管理不善。政府通常更关心储量的数量和总面积,而不是它们的有效性(Xu和Melick 2007)。例如,在甘孜,51个自然保护区中有50个是在1995年之后建立的(环境保护部(MEP) 2010),但到2004年,指派管理42个自然保护区的人员不足10人(Li 2007)。相比之下,当地社区有强烈的意愿保护他们的神山,但由于中国的国有土地所有制制度,没有管理权力(Xu和Melick 2007)。甘孜境内几乎没有一个保护区不包含人类住区,我们认为将当地社区排除在保护区的决策过程之外只会导致冲突。神山与自然保护区的高度重叠表明,通过利用当地民众的支持,当地社区与自然保护区的共同管理有可能提高保护区的有效性。
Xu和Melick(2007)提出了一种保护特许的方法,以管理中国当地社区保护的国有土地。2006年,我们在西藏地区启动了“保护协议”项目,由自然保护区和当地林业部门通过保护协议,将部分国有土地的经营权移交给当地社区。制定了管理计划和监测指标。保护组织为当地社区提供能力建设,地方政府为其保护活动提供年度小额奖励。初步经验表明,保护特许经营的方式相对来说具有成本效益,可以作为一种采用传统机构的方式,以补充西藏地区的官方保护网络(Shen et al. 2007)。尽管最初的谈判需要时间和人力和财力资源,但一旦达成协议,保护国有土地的管理成本可以很大程度上转嫁到当地社区(Ma and Basang Lhamo 2009)。由于当地资源管理实践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维护和现有的自愿保护努力相一致,机会成本很低(Ma和Basang Lhamo 2009)。对于那些对保护土地和野生动物有着强烈承诺的传统藏族社区,补偿机制需要精心设计,以避免保护活动从自愿转向利益驱动的风险,外部支付削弱了内部动机(Wunder et al. 2008)。藏区保护租界永续的关键是当地社区保护权利的延续。在法律上承认保护特许权的做法,例如中国正在制定的《保护区法》,并需要稳定的财政资源来确保其更广泛的应用和可持续性。
为了促进当地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我们建议:(1)自然保护区管理者识别保护区内的圣地并绘制地图,确定主要的传统管理机构,增加他们对自然资源使用的传统限制和当地社区实际使用自然资源的认识。健全的管理应该基于对传统做法的理解和尊重,并让当地社区参与决策过程(Xu和Melick 2007);(2)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引入传统方法,从而在藏族传统社区中采用保护目标(Xu et al. 2005, Bhagwat and Rutte 2006)。例如,如果保护区的边界用仪式使之神圣化,并用经幡或其他宗教符号加以标记,就会获得当地人的尊重。通过宗教仪式,由仁波切进行的保护教育将更受当地人的欢迎。甚至可以为了保护目的而建立新的圣山(Ma 2005)。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管理体制有其局限性。传统规则的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机构。当修道院力量薄弱时,这些规则可能会被松散地执行。如果大量的人来朝拜,管理不善的朝拜会导致栖息地退化(Shinde 2007)。一些传统上允许在圣山上进行的活动可能是破坏性的,比如草药采集和放牧。受近几十年市场需求增长的驱动,特别是松茸和虫草冬虫夏草作为食物和传统药物,资源的不可持续使用和过度的人类干扰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和栖息地的退化(Salick et al. 2005, Amend et al. 2010)。为推广传统做法在保育方面的作用,有必要恢复文化传统,并协助当地社区制定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新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最后,我们强调了西藏圣地在保护中的重要性,因为西藏人居住的土地与多个国家和四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即中国东南部的山脉、中亚的山脉、喜马拉雅东部和印度-缅甸)重叠(Myers and Mittermeier et al. 2000, Mittermeier et al. 2004)。在未来的保护规划和管理中,认识到圣地保护的传统做法并将其纳入其中,将极大地促进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因此具有全球意义。
致谢
首先,我们感谢西藏当地人民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传统知识,并为我们的实地工作提供了后勤支持。我们感谢刘伟、丁晓涛、蒋振仁、李斌杰、骆波加塔以及所有为数据收集做出贡献的人。我们也感谢扎西多杰、长永彭措、次仁吉美、穆索等人就西藏传统知识进行的咨询。本研究得到了蓝月亮基金的资助,由北京大学、保护国际中国项目、四川省森林调查与规划研究所、甘孜州林业厅和绿康联合开展。我们感谢自然与社会中心的同事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深思熟虑的讨论。我们感谢W. J. McShea, G. Schaller和S. Li对手稿的帮助。
文献引用
修正,A.,方之,C.易,W. C.麦克拉奇。2010.在中国云南西北部,当地人对松茸管理的看法。生物保护143:165 - 172。D. M.安德森,J.萨利克,R. K.莫斯利和X. K. Ou。2005。保护神药山:滇西北藏族圣地植被分析。生物多样性和保护14:3065 - 3091。http://dx.doi.org/10.1007/s10531-004-0316-9
贝尔克斯,J. Colding和C. Folke, 2000。重新发现传统生态知识作为适应性管理。生态应用程序10(5): 1251 - 1262。http://dx.doi.org/10.1890/1051 - 0761 (2000) 010 (1251: ROTEKA) 2.0.CO; 2
S. A.巴格瓦特,C. G.库什拉帕,P. H.威廉姆斯,N. D.布朗。印度西高止山脉神圣树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方法。保护生物学19:1853 - 1862。http://dx.doi.org/10.1111/j.1523-1739.2005.00248.x
S. A.巴格瓦特,C. G.库什拉帕,P. H.威廉姆斯,N. D.布朗。2005b。非正式保护区在维持印度西高止山脉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生态和社会10(1): 8。(在线)网址://www.dpl-cld.com/vol10/iss1/art8/
Bhagwat, S. A.和C. Rutte, 2006。圣林:生物多样性管理的潜力。生态学与环境前沿“,10:519 - 524。http://dx.doi.org/10.1890/1540 4 - 9295 (2006) [519: SGPFBM] 2.0.CO; 2
Bossart, J. L., E. Opuni-Frimpong, S. Kuudaar和E. Nkrumah. 2006。加纳圣林和森林保护区果实食用型蝴蝶物种的丰富度、丰富性和互补性。生物多样性和保护15:333 - 359。http://dx.doi.org/10.1007/s10531-005-2574-6
Castro V.和C. Aldunate. 2003。安第斯山脉中南部高地的圣山。山地研究与开发23:73 - 79。http://dx.doi.org/10.1659/0276 - 4741 (2003) 023 (0073: SMITHO) 2.0.CO; 2
钱伯斯,r . 1994。参与式农村评价的起源与实践。世界发展22:953 - 969。http://dx.doi.org/10.1016/0305 - 750 x (94) 90141 - 4
柯尔丁和C.福尔克。2001。社会禁忌:地方资源管理和生物保护的“隐形”系统。生态应用程序11:584 - 600。
甘孜州志委员会。1997.甘孜史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成都
戴,g . 2007。甘孜州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康定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6:18-23
丹尼尔斯,R. J. R., S.钱德兰,M.加吉尔,1993。保护南印度Uttara-Kannada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战略。环境保护20:131 - 138。http://dx.doi.org/10.1017/S0376892900037620
Decher, j . 1997。保护,小型哺乳动物,以及西非神圣树林的未来。生物多样性和保护6:1007 - 1026。http://dx.doi.org/10.1023/A:1018991329431
杜德利,N. L. Higgins-Zogib和S. Mansourian. 2006。超越信仰:连接信仰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区。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宗教与保护联盟,瑞士格兰。
杜德利,N., L. Higgins-zogib和S. Mansourian. 2009。保护区、信仰和神圣自然场所之间的联系。保护生物学23:568 - 577。http://dx.doi.org/10.1111/j.1523-1739.2009.01201.x
冯,z . 2005。藏传佛教的保护观。83 - 89页在马建中、陈建中,编辑。西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云南。
加吉尔,M.和V. D.瓦尔塔克,1974。印度西高止山脉神圣的小树林。经济植物学30(2): 152 - 160。http://dx.doi.org/10.1007/BF02862961
哈里斯,1991年。中国青海南部麝和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前景。山地研究与开发11(4): 353 - 358。http://dx.doi.org/10.2307/3673718
何建华。2005。西藏苯教在保护中的作用。68 - 72页在马建中、陈建中,编辑。西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云南。
黄明华,2003。台湾玉山国家公园亚洲黑熊生态学与人熊互动.论文,明尼苏达大学,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美国。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1994.保护区管理类别指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英国剑桥和瑞士格兰德。
贾恩,H. B.辛格,S. C.拉伊和E.夏尔马,2004。印度锡金喜马拉雅地区神圣的khecheopalri湖的民间传说:保护环境的呼吁。亚洲民俗研究63:219 - 302。
贾米尔,S. A.和H. N.潘迪。2003。印度东北部Jaintia山神圣树林中的维管植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保护12:1497 - 1510。http://dx.doi.org/10.1023/A:1023682228549
贾姆索,2005。西藏传统文化的生态观念。康定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4:12-16。
库弗,J., N.格鲁伯和M.海因里希。2006。危地马拉东部的可可——一种具有生态意义的圣树。环境、发展与可持续性8:597 - 608。http://dx.doi.org/10.1007/s10668-006-9046-3
李淑贞,2007。作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方式的保护特许权。农村经济8:26-28。
李斌,杨凤英,孙胜,穆胜,张志勇,沈旭林,陆志勇。2008。西南地区社区保护区研究综述。 在 社区保护区:2003年德班和2004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P7后的全球现状和需求回顾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经济和社会政策委员会(CEESP)和世界保护区委员会(WCPA),瑞士Gland。(在线)网址:http://cmsdata.iucn.org/downloads/sw_china_cca_study.pdf.
刘建刚,欧阳宗英,皮姆s.l.,雷文p.h.,王宪昆,苗浩,韩乃银。2003。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300:1240 - 1241。http://dx.doi.org/10.1126/science.1078868
罗鹏,裴世杰,徐建昌。2001。云南圣地及其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山地科学杂志19:327 - 333。
马建忠。2005。卡瓦卡波山的自然圣地和保护。页面33-40在马建中、陈建中,编辑。西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云南。
马h。B。巴桑拉莫。2009。保护租界:三江源保护的新途径。青海经济研究2:35-39。
Maharana, I, S. C. Rai和E. Sharma, 2000。印度锡金喜马拉雅圣湖的生态旅游价值。环境保护27:269 - 277。http://dx.doi.org/10.1017/S0376892900000308
Malhotra, K. C. 2001。印度神圣树林的文化和生态层面。印度国家科学院,新德里和英迪拉·甘地Rashtriya Manav Sangrahalaya博帕尔。
马格莱斯,c.r,和R. L.普雷斯,2000。系统保护规划。自然405:243 - 253。http://dx.doi.org/10.1038/35012251
Mgumia, F. H.和G.欧巴。2003。圣林在坦桑尼亚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潜在作用。环境保护30:259 - 265。http://dx.doi.org/10.1017/S0376892903000250
环境保护部。2010.四川省自然保护区2009。环境保护部,中国北京。(在线)网址:http://sts.mep.gov.cn/zrbhq/zrbhq/201012/t20101220_198880.htm
中国环境保护部。2008.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中国环境保护部,中国北京。
米特迈尔,R. A, P. R.吉尔,M.霍夫曼,J. Pilgrim, T. Brooks, C. G.米特迈尔,J. Lamoreux, G. A. B. da Fonseca. 2004。热点回顾.墨西哥CEMEX。
迈尔斯,N.和R. A. Mittermeier. 2000。生物多样性热点是保护重点。自然403:853。http://dx.doi.org/10.1038/35002501
南文云。2001a。藏族古代自然崇拜的观念与功能。青海民族研究12:23-31。
南文云。2001b。藏区禁忌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西北少数民族研究3:21-29。
北华盛顿,1990年。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剑桥大学出版社,英国剑桥。
诺顿p.m.和A. B.劳森,1985。用无线电追踪开普省斯泰伦博斯地区的豹子和野猫。南非野生动物研究杂志15:17-24。
奥维耶多,g . 2006。南美洲的社区保护区。页面47-55在a . Kothari编辑器。社会保守区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腺、瑞士。
Ramanujam, m.p和k.p k Cyril. 2003。南印度本地治里地区四个神圣树林的木本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保护12:289 - 299。http://dx.doi.org/10.1023/A:1021926002101
里德,江明,滕琼,秦铮,胡杰。1991。亚洲黑熊生态学(熊属主干)在中国四川。哺乳动物55:221 - 238。http://dx.doi.org/10.1515/mamm.1991.55.2.221
萨利克,J. A. Amend, D. Anderson, K. Hoffmeister, B. Gunn,和方志东。2007。西藏的圣地保存着古老的树木,覆盖在喜马拉雅东部。生物多样性和保护16:693 - 706。http://dx.doi.org/10.1007/s10531-005-4381-5
杨宇平,杨宇平,杨宇平。修订。2005。喜马拉雅东部卡瓦卡波附近的西藏土地利用变化。经济植物学59:312 - 325。http://dx.doi.org/10.1663/0013 - 0001 (2005) 059 (0312: TLUACN) 2.0.CO; 2
沈、x L。s . z . Li f .田,z。2007。中国西部环境保护的新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所》193-215页,主编。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卷。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中国
辛德,K. N. 2007。朝圣与环境:朝圣中心的挑战。beplay官网世界杯旅游业当前的问题(4): 343 - 365。http://dx.doi.org/10.2167/cit259.0
史密斯,d . 2006。澳大利亚的土著保护区。14到20页在a . Kothari编辑器。社会保守区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腺、瑞士。
Tengö, M. K.约翰逊,F. Rakotondrasoa, J. Lundberg, J. a。Andriamaherilala,工业大学。Rakotoarisoa和T. Elmqvist. 2007。禁忌与森林治理:马达加斯加南部热点干燥森林的非正式保护。中记录36:683 - 691。http://dx.doi.org/10.1579/0044 36 - 7447 (2007) [683: TAFGIP] 2.0.CO; 2
Tischendorf, L.和L. Fahrig. 2000。景观连通性的使用与测量。Oikos90:7-19。http://dx.doi.org/10.1034/j.1600-0706.2000.900102.x
Wadley, R. L.和C. J. P. Colfer. 2004。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的神圣森林、狩猎和保护。人类生态学32:313 - 338。http://dx.doi.org/10.1023/B:HUEC.0000028084.30742.d0
文德尔,S. B.坎贝尔,P. G. H.弗罗斯特,J. A.塞耶,R.伊万,L.渥伦伯格。2008。当捐助者临场退缩时:在印尼加里曼丹的塞土郎(Setulang,加里曼丹)的社区保护租界从未发生过。生态和社会13(1): 12。(在线)的URL: //www.dpl-cld.com/vol13/iss1/art12/
张建峰,徐慧敏,郭宏。2008。香格里拉藏族圣山与普通山植被对比中国西部林业科学(2): 37 46-50
谢,y 2004。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研究综述。页面33-51在谢阳、王s、彼得,编辑。中国的保护区。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北京。
徐建春,马东泰,傅玉生,吕铮,马立克。2005。整合神圣知识保护: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与景观。生态和社会10:7。(在线)网址://www.dpl-cld.com/vol10/iss2/art7/
徐建昌,D. R.梅里克,2007。西南地区公共保护区有效性的再思考。保护生物学21:318 - 328。http://dx.doi.org/10.1111/j.1523-1739.2006.00636.x
张荣忠,1997。横断山脉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北京。
邹丽娟,谢志强,欧小康。2005。西藏神山在云南香格里拉峡谷自然保护中的意义。生物多样性科学13 (1): 51-57


